画地为牢(小说)
胡棪荣(25岁)中国科学院大学昆明植物研究所硕士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9月15日 07版)
凌晨
离心机嗡鸣着,刚从冰箱拿出的培养液在瓶身上凝出细密的水雾,薛棪的手机蓦地在实验台上震动起来,她摘下手套去拿,跃动的消息上方,屏幕上显示6点整。
这个点,父亲应该已经在医院躺下,等着粗厚针头插入他手臂上狰狞的瘘管,就像一台迫切需要加油却永远加不满的车。
“丫头,上次说那个科长的儿子……”薛棪按住语音键:“都说了我有对象。”她抬眼看了看离心机,转速已经降到8000转。母亲很快又发来一句话:“反正我到现在没和身边人说你谈对象,这些优质股还是要了解一下的。”附在消息最后的,是一个呲牙笑的表情。
薛棪没回复,转头给周景訸发去一句“生日快乐”便摁灭了手机。
母亲总这样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女儿很好,怎么都不应该找一个个子不算高、薪水也平平的男友。她也总是坚信她的女儿结婚生子才能获得幸福,尽管她自己并没有嫁给爱情,只是嫁给了“也到年纪了”“你外公很满意这个小伙子”的外界期许。
随后,这段婚姻又被迅速地套上了更大的义务枷锁,母爱将她牢牢捆在了一个多病的男人和恶毒的婆婆身边。她成为家政超人,可谁还记得她曾经也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女?这种自愿的牺牲总压得薛棪喘不过气,有时候她甚至希望她没有出生,也许这样一切都会不同,至少她的存在不会成为她父亲重病时束缚住母亲的锁链。
这样的想法对她父亲太残忍,但她既抑制不住这样的想法,又在那样的可能性里煎熬,自责不已。
所以为什么要结婚?她想着,也真这么问了。微信那头输入许久,最后母亲很认真地回答:“不然老了只有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午间
寝室门推开的瞬间,冷气裹着李小凤的凉拖卷了进来,吹散了薛棪的睡意。
“昨天又熬夜做实验了?”李小凤没抬头,把食堂打回的饭掷在自己桌上坐下,手指无意中碰到鼠标,亮起屏幕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参考文献。
“嗯。”
薛棪把咖啡倒进水中晃了晃,液体撞击杯壁的声音让她想起高中。她和同桌原筱总是在课后一边泡咖啡一边交流学习心得,但交流更多的却是如何用各色胶带和颜色淡雅的荧光笔把错题本做好看,以为这样就能将知识和人生收入囊中——她突然想笑。
“我爸又在吐槽我姐管他要钱。”她点开语音外放,薛棪听不懂,只听到那激愤的男声背景音是嘈杂的鸡鸣牛哞。她张开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平常总是强大又独立、此刻却显出几分无助的女孩。倒是小凤自顾自地继续说了起来:“穷成这样还要搞入赘,两个人拿不出6万块还折腾做试管,太可笑了。而且他和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想让我站他那边骂我姐?”
她想了想,又补充道:“算了,我和我姐也不是一边。”
薛棪常用的香水让李小凤想起记忆里的焚香。那年奶奶出殡,入赘的姐夫作为“长孙”捧灵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头,她父亲作为长子举着幡,她和姐姐以及堂姐妹们远远地在队伍最后缀着,唢呐声刺破了大理的云。她总忍不住想,为何同样是养老的工具,却可以被受益者嫌弃至此,原来缺的不只是儿子,更是一种古旧带着腐烂气息的尊严。
窗帘被风吹进室内,李小凤突然想改论文致谢,她以为她的心早已被磨成灰烬,直到那些话语如火星般溅起来,才知道灰烬下还埋着会疼的血肉。原来他们爱的从不是自己的子女,而是儿女为他们献祭一切时战栗的灵魂弧光。而她其实早就知道的,不是吗?
下午
窗外的风像低声呜咽。薛棪只合眼一小时,又拖着身子回实验楼。她不想告诉任何人自己曾想去国外继续深造,只默默在租房网上刷着靠近上海某著名医院的蜗居——只要付出一点梦想的代价,就可以离愧疚很远。
青松的影子碎在实验楼的玻璃门上,耀眼的阳光却扎不进走廊。手机一震,是周景訸丢来的两个字:
“想死。”
薛棪皱了皱眉,不假思索:“又和你爸妈吵架了。”是肯定的语气。这句话仿佛打开了对面的话匣子:“真是烦死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和朋友们晚上出来,这就叫瞎混吗?我不知道要努力学习吗?但就不能偶尔让我喘口气吗?非要今天骂我?……”
吐槽的话语没头没尾,夹杂着许多粗鄙的骂声,带着薛棪回到大二的那一天。坐在漆黑的宿舍楼下,她沉默地拍着和父母因为一些小事就吵得情绪崩溃的周景訸,那是那个自信又搞笑的女孩唯一一次在她面前哭到喘不上气。想起“共友”(两个人或者更多人所共同拥有的朋友)前几日还吐槽周景訸“她自己也知道自己有钱、有颜、一天天还瞎焦虑”,像一只宠物猫向流浪狗声称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丛林。但她明白,周景訸并不是在炫耀和无病呻吟,只是天堂和地狱隔得太远,彼此都听不懂内心呜咽的字句。
周景訸跌坐在出租屋的榻榻米上。她伸手够到没来得及吃的冰激凌蛋糕——已经融化,散发出甜腻的气息,混合着威士忌的气味令她作呕——明明想吃这一款蛋糕很久了。她想起17岁那个雪夜,初恋和其余同学一起把她的湖南口音编成顺口溜,笑她是高考移民,班主任当着全班训斥她:“你爸妈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早恋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谁?”那里不是家乡,那里有很多人,却没有一颗心贴近她。嘴里的蛋糕化作胶水,无声了她喉中的呜咽。
“他们从没问我要不要这些。”周景訸发来最后一句。谁又问过她呢?薛棪盯着屏幕,想起自己那句“想去国外”刚出口,父亲便说:“女孩子跑那么远太危险了。你弟弟是男孩子,以后出去闯我肯定不会舍不得。”
如此双标的爱,却将她捆得这般紧。
至少父母在其他地方还是对她和弟弟一视同仁地爱着不是吗?他们的矛盾也只是源于旧社会微弱却顽固存在的投影。小凤对她的自我安慰总嗤之以鼻,这个从绝对重男轻女的家庭走出来的姑娘,面对父母有着更加坚决和对立的态度,不够爱就是不爱。薛棪做不到她这样。
暮色
原筱的微信电话打来时,薛棪正在给小白鼠换垫料。视频里上海陆家嘴的霓虹在暴雨中晕成色块,原筱的珍珠耳钉在镜头前晃:“宝,我们准备去日本玩。”
“马上要出初试分了。不等出分再去?”
“他怕真三战还考不上就没有心情玩了。”
薛棪想起高中晚自习,她和原筱总是躲在全班琅琅的书声下聊着天,那时幻想中的未来总是可期,无关学历、家境。而后,一个在父亲“爸爸的身体实在没法再陪你苦一年”的哀求话语里断了复读的念头,另一个却因为没考上“985”“211”大学被觉得丢脸的父亲逼着在大一的国庆节卷铺盖回来复读。
此刻那个复读考上好学校的女孩眼角填满了愁绪,依旧是因为学历:“我前两天还去他家见他爸妈了,我爸妈还不知道我谈恋爱。”
“没事,他今年考上就能和你父母公开了吧。”
“但愿吧。”打扮精致的姑娘想了想,“其实我也有点受不了他就是个普通一本,我也不好意思告诉我爸。我还在想难道结婚后真的要去他那里吗?妈呀,我都不敢想。”外地人,普通一本,还不像自己女儿保研上岸,就算考研上岸,也早就踩了父母的好几道红线。
“是啊。”薛棪附和着,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她删除了国外发来的邮件,和父母畅想着她既定的未来:“上海离家近,周末都能回来。上海医疗条件也好……”那时父母脸上绽开了那么璀璨的笑。
由衷地,她从那笑容中汲取到了幸福和力量——这就够了。
离心机滴滴作响,与7年前父亲确诊尿毒症时的救护车鸣笛重叠,那时的她只能站在那里看着,痛恨于自己的无力。她忽然明白,人生就像离心的样本,总有些东西要沉在管底。就像每次周景訸或李小凤和她说着女权等话题时,她回应的、内心想的、自己真正做的,从来都没统一过——她把自己撕裂成了三体世界里的3颗太阳,于是烈日焚心,倒不如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决定。人生最后终会坍缩为唯一的选项,也许自愿把人生之路裁成单行线也好——她其实早就下定了决心,却总忍不住去想被放弃的另一些可能。换个角度想,有万千选择的人,遗憾也不会比只有几种选择的人更少。
那头原筱还在说着:“哎,宝,你都不知道这两天我找工作多难,大公司现在居然面试前还要笔试,还考数学题,高中毕业之后我都800年没做过了。哎,你说那些小城市的人都怎么找工作啊……”
子夜
晚风彻骨。薛棪走出实验室,保安的手电筒正扫过漆黑的夜。这时候的原筱已经坐上去日本的飞机,海那边的周景訸不知是否又在携友买醉?她又想到小凤,那个姑娘不再执着于晚上不断打电话劝姐姐先赚钱别急着备孕后,此时应该也已早早睡下了。
她蹑手蹑脚地打开宿舍门,漆黑的屋子里,只有李小凤的电脑屏幕微微亮着。她瞥了一眼,那毕业论文的致谢里没有父母,没有导师,只有自己。薛棪想起高中语文老师说的“庄周梦蝶”,如果可以,蝶真的会想成为庄周吗?对于蝴蝶来说,庄周说不定是另一只挣扎着破茧的蝴蝶,只是世界上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丝笼,每只蝴蝶都有自己的茧房要破。
宿舍门锁咬合的瞬间,陷入床褥的那一刻,一首歌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是歌剧《猫》中的《Memory》。她无声哼唱起那熟悉的曲调。手机屏幕亮起母亲的信息——又一条关于婚姻生活经营的鸡汤。脑海中,走廊尽头,李小凤的螺蛳粉还在桌上冒着香气,原筱的高跟鞋并排立在鞋柜,周景訸的和室拉门反射着手机屏幕的蓝光,像4块块破碎的镜子,拼凑出凌晨3点的完整。
胡棪荣(25岁)中国科学院大学昆明植物研究所硕士生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9月15日 07版
凌晨
离心机嗡鸣着,刚从冰箱拿出的培养液在瓶身上凝出细密的水雾,薛棪的手机蓦地在实验台上震动起来,她摘下手套去拿,跃动的消息上方,屏幕上显示6点整。
这个点,父亲应该已经在医院躺下,等着粗厚针头插入他手臂上狰狞的瘘管,就像一台迫切需要加油却永远加不满的车。
“丫头,上次说那个科长的儿子……”薛棪按住语音键:“都说了我有对象。”她抬眼看了看离心机,转速已经降到8000转。母亲很快又发来一句话:“反正我到现在没和身边人说你谈对象,这些优质股还是要了解一下的。”附在消息最后的,是一个呲牙笑的表情。
薛棪没回复,转头给周景訸发去一句“生日快乐”便摁灭了手机。
母亲总这样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女儿很好,怎么都不应该找一个个子不算高、薪水也平平的男友。她也总是坚信她的女儿结婚生子才能获得幸福,尽管她自己并没有嫁给爱情,只是嫁给了“也到年纪了”“你外公很满意这个小伙子”的外界期许。
随后,这段婚姻又被迅速地套上了更大的义务枷锁,母爱将她牢牢捆在了一个多病的男人和恶毒的婆婆身边。她成为家政超人,可谁还记得她曾经也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女?这种自愿的牺牲总压得薛棪喘不过气,有时候她甚至希望她没有出生,也许这样一切都会不同,至少她的存在不会成为她父亲重病时束缚住母亲的锁链。
这样的想法对她父亲太残忍,但她既抑制不住这样的想法,又在那样的可能性里煎熬,自责不已。
所以为什么要结婚?她想着,也真这么问了。微信那头输入许久,最后母亲很认真地回答:“不然老了只有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午间
寝室门推开的瞬间,冷气裹着李小凤的凉拖卷了进来,吹散了薛棪的睡意。
“昨天又熬夜做实验了?”李小凤没抬头,把食堂打回的饭掷在自己桌上坐下,手指无意中碰到鼠标,亮起屏幕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参考文献。
“嗯。”
薛棪把咖啡倒进水中晃了晃,液体撞击杯壁的声音让她想起高中。她和同桌原筱总是在课后一边泡咖啡一边交流学习心得,但交流更多的却是如何用各色胶带和颜色淡雅的荧光笔把错题本做好看,以为这样就能将知识和人生收入囊中——她突然想笑。
“我爸又在吐槽我姐管他要钱。”她点开语音外放,薛棪听不懂,只听到那激愤的男声背景音是嘈杂的鸡鸣牛哞。她张开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平常总是强大又独立、此刻却显出几分无助的女孩。倒是小凤自顾自地继续说了起来:“穷成这样还要搞入赘,两个人拿不出6万块还折腾做试管,太可笑了。而且他和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想让我站他那边骂我姐?”
她想了想,又补充道:“算了,我和我姐也不是一边。”
薛棪常用的香水让李小凤想起记忆里的焚香。那年奶奶出殡,入赘的姐夫作为“长孙”捧灵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头,她父亲作为长子举着幡,她和姐姐以及堂姐妹们远远地在队伍最后缀着,唢呐声刺破了大理的云。她总忍不住想,为何同样是养老的工具,却可以被受益者嫌弃至此,原来缺的不只是儿子,更是一种古旧带着腐烂气息的尊严。
窗帘被风吹进室内,李小凤突然想改论文致谢,她以为她的心早已被磨成灰烬,直到那些话语如火星般溅起来,才知道灰烬下还埋着会疼的血肉。原来他们爱的从不是自己的子女,而是儿女为他们献祭一切时战栗的灵魂弧光。而她其实早就知道的,不是吗?
下午
窗外的风像低声呜咽。薛棪只合眼一小时,又拖着身子回实验楼。她不想告诉任何人自己曾想去国外继续深造,只默默在租房网上刷着靠近上海某著名医院的蜗居——只要付出一点梦想的代价,就可以离愧疚很远。
青松的影子碎在实验楼的玻璃门上,耀眼的阳光却扎不进走廊。手机一震,是周景訸丢来的两个字:
“想死。”
薛棪皱了皱眉,不假思索:“又和你爸妈吵架了。”是肯定的语气。这句话仿佛打开了对面的话匣子:“真是烦死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和朋友们晚上出来,这就叫瞎混吗?我不知道要努力学习吗?但就不能偶尔让我喘口气吗?非要今天骂我?……”
吐槽的话语没头没尾,夹杂着许多粗鄙的骂声,带着薛棪回到大二的那一天。坐在漆黑的宿舍楼下,她沉默地拍着和父母因为一些小事就吵得情绪崩溃的周景訸,那是那个自信又搞笑的女孩唯一一次在她面前哭到喘不上气。想起“共友”(两个人或者更多人所共同拥有的朋友)前几日还吐槽周景訸“她自己也知道自己有钱、有颜、一天天还瞎焦虑”,像一只宠物猫向流浪狗声称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丛林。但她明白,周景訸并不是在炫耀和无病呻吟,只是天堂和地狱隔得太远,彼此都听不懂内心呜咽的字句。
周景訸跌坐在出租屋的榻榻米上。她伸手够到没来得及吃的冰激凌蛋糕——已经融化,散发出甜腻的气息,混合着威士忌的气味令她作呕——明明想吃这一款蛋糕很久了。她想起17岁那个雪夜,初恋和其余同学一起把她的湖南口音编成顺口溜,笑她是高考移民,班主任当着全班训斥她:“你爸妈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早恋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谁?”那里不是家乡,那里有很多人,却没有一颗心贴近她。嘴里的蛋糕化作胶水,无声了她喉中的呜咽。
“他们从没问我要不要这些。”周景訸发来最后一句。谁又问过她呢?薛棪盯着屏幕,想起自己那句“想去国外”刚出口,父亲便说:“女孩子跑那么远太危险了。你弟弟是男孩子,以后出去闯我肯定不会舍不得。”
如此双标的爱,却将她捆得这般紧。
至少父母在其他地方还是对她和弟弟一视同仁地爱着不是吗?他们的矛盾也只是源于旧社会微弱却顽固存在的投影。小凤对她的自我安慰总嗤之以鼻,这个从绝对重男轻女的家庭走出来的姑娘,面对父母有着更加坚决和对立的态度,不够爱就是不爱。薛棪做不到她这样。
暮色
原筱的微信电话打来时,薛棪正在给小白鼠换垫料。视频里上海陆家嘴的霓虹在暴雨中晕成色块,原筱的珍珠耳钉在镜头前晃:“宝,我们准备去日本玩。”
“马上要出初试分了。不等出分再去?”
“他怕真三战还考不上就没有心情玩了。”
薛棪想起高中晚自习,她和原筱总是躲在全班琅琅的书声下聊着天,那时幻想中的未来总是可期,无关学历、家境。而后,一个在父亲“爸爸的身体实在没法再陪你苦一年”的哀求话语里断了复读的念头,另一个却因为没考上“985”“211”大学被觉得丢脸的父亲逼着在大一的国庆节卷铺盖回来复读。
此刻那个复读考上好学校的女孩眼角填满了愁绪,依旧是因为学历:“我前两天还去他家见他爸妈了,我爸妈还不知道我谈恋爱。”
“没事,他今年考上就能和你父母公开了吧。”
“但愿吧。”打扮精致的姑娘想了想,“其实我也有点受不了他就是个普通一本,我也不好意思告诉我爸。我还在想难道结婚后真的要去他那里吗?妈呀,我都不敢想。”外地人,普通一本,还不像自己女儿保研上岸,就算考研上岸,也早就踩了父母的好几道红线。
“是啊。”薛棪附和着,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她删除了国外发来的邮件,和父母畅想着她既定的未来:“上海离家近,周末都能回来。上海医疗条件也好……”那时父母脸上绽开了那么璀璨的笑。
由衷地,她从那笑容中汲取到了幸福和力量——这就够了。
离心机滴滴作响,与7年前父亲确诊尿毒症时的救护车鸣笛重叠,那时的她只能站在那里看着,痛恨于自己的无力。她忽然明白,人生就像离心的样本,总有些东西要沉在管底。就像每次周景訸或李小凤和她说着女权等话题时,她回应的、内心想的、自己真正做的,从来都没统一过——她把自己撕裂成了三体世界里的3颗太阳,于是烈日焚心,倒不如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决定。人生最后终会坍缩为唯一的选项,也许自愿把人生之路裁成单行线也好——她其实早就下定了决心,却总忍不住去想被放弃的另一些可能。换个角度想,有万千选择的人,遗憾也不会比只有几种选择的人更少。
那头原筱还在说着:“哎,宝,你都不知道这两天我找工作多难,大公司现在居然面试前还要笔试,还考数学题,高中毕业之后我都800年没做过了。哎,你说那些小城市的人都怎么找工作啊……”
子夜
晚风彻骨。薛棪走出实验室,保安的手电筒正扫过漆黑的夜。这时候的原筱已经坐上去日本的飞机,海那边的周景訸不知是否又在携友买醉?她又想到小凤,那个姑娘不再执着于晚上不断打电话劝姐姐先赚钱别急着备孕后,此时应该也已早早睡下了。
她蹑手蹑脚地打开宿舍门,漆黑的屋子里,只有李小凤的电脑屏幕微微亮着。她瞥了一眼,那毕业论文的致谢里没有父母,没有导师,只有自己。薛棪想起高中语文老师说的“庄周梦蝶”,如果可以,蝶真的会想成为庄周吗?对于蝴蝶来说,庄周说不定是另一只挣扎着破茧的蝴蝶,只是世界上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丝笼,每只蝴蝶都有自己的茧房要破。
宿舍门锁咬合的瞬间,陷入床褥的那一刻,一首歌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是歌剧《猫》中的《Memory》。她无声哼唱起那熟悉的曲调。手机屏幕亮起母亲的信息——又一条关于婚姻生活经营的鸡汤。脑海中,走廊尽头,李小凤的螺蛳粉还在桌上冒着香气,原筱的高跟鞋并排立在鞋柜,周景訸的和室拉门反射着手机屏幕的蓝光,像4块块破碎的镜子,拼凑出凌晨3点的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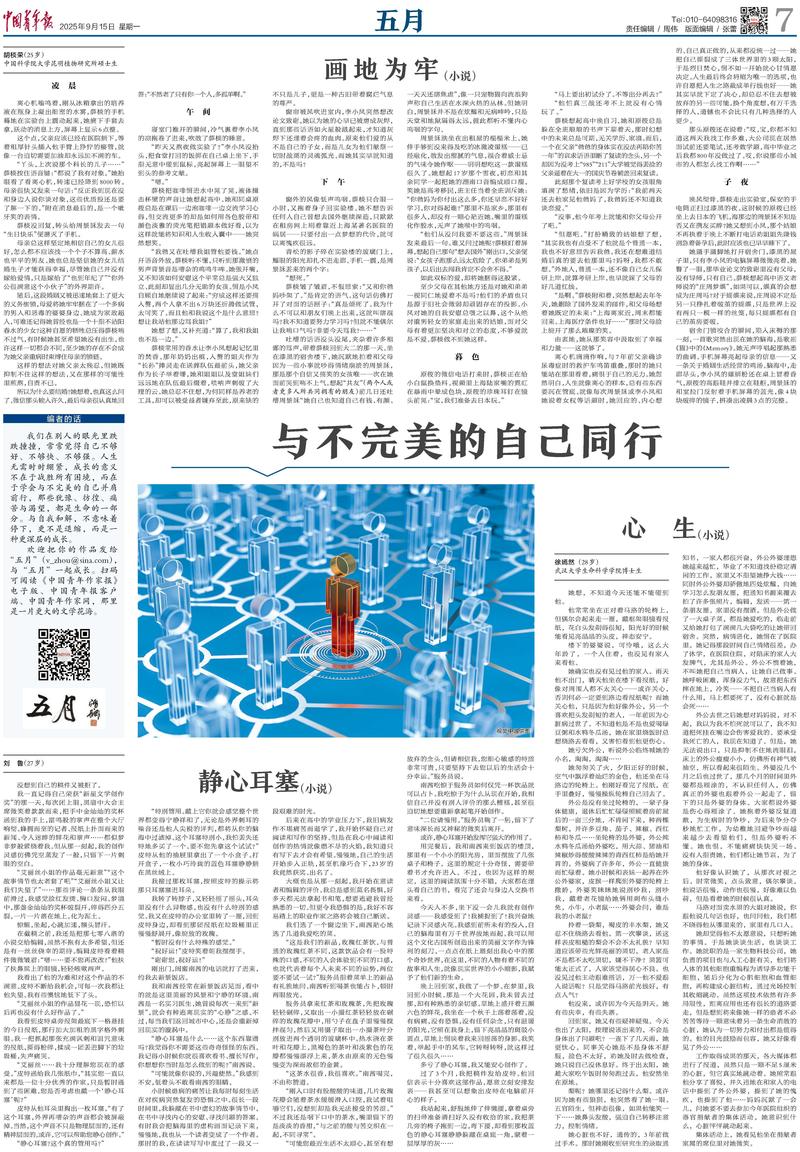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