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以前,我都住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了解自然的途径主要靠色彩斑斓的显示屏。我时常幻想宽阔无垠的草原或是绵延起伏的高山会是我素未谋面的家乡。直到某个暑假,我随父母乘坐老式客船去一座海岛,我得以见到一片望不尽的海。
我不太喜欢海,闻见父母身上的咸腥海风,总觉得盐晶颗粒从骨头里长了出来。还有那摸不清楚的海潮,即便紧紧跑在父亲身后,浪也总是能打在脚踝上,生疼。
所以我坐在远处的石头上,遥遥看海。
我一人看海,有人看到了我。他是彭家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小海。他比我大3岁,性格开朗像有无尽活力。小海哥把我拉进小团体中,我们奔跑过小岛的每寸土地,越跑越快,化作了风穿过大广场,穿过百年宗祠。
我止步在大海前。
“嘉!过来!”小海哥高声喊着。他身后的人也随之呼喊起来,耳边哪里还听得到海风呼呼。少男少女的诚挚烧干了冰冷,我终于大胆起来,走向那片海。
天下起雨,孩童的惊呼声与雷声相伴,欲与天争一个气势高低。我们拉住彼此跑回家,路上我把膝盖磕得血肉模糊,但挨父母的责骂时却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在那个下午,听不太明白的乡音唤着我,教我识别贝壳,教我读懂潮汐规律,我突然认识了大海,然后同它和好,转头看稚嫩柔善的脸庞在身侧,有什么比这些更解不开偏见的。
自那次后我常去找小海哥他们玩,可父母唠叨说玩乐不是长久之事,不如抓紧时间看看书、努努力。我不能顺从他们的话,此刻的玩乐不是命运对我这个年纪的宽宏允许吗?父母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小海哥他们出不了岛,是没出息的人。
我很生气,出息由什么定义?是向上寻求的代代期望,还是向下对未知前方的忧虑?
我再次去找小海哥玩,还没到门口,却见他慌忙闯出。朱家的小弟和家里闹矛盾找不见了人影,伙伴们满岛寻找,终于在一处岩石的缝隙处发现他。小海哥最为聪明冷静,他一边安排人叫大人,一边让大家把衣服脱下给他保暖。待把人拉上来的时候,又发现小弟脚踝受了伤,小海哥好像生来什么都知道,他固定并包扎伤口再背起人朝最快回家的小路上走去。
阴冷的雨里,我们追逐着他如同追着唯一的火光。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出息?
小海哥成绩优异,我有许多解不开的题目他都能帮忙作答。可惜碍于各种条件,他去了离岛最近的普通中学。以前,我会带一种无缘由的怜悯去看他们这些岛上的孩子——海的无界似有界,将他们拦在此处。可见过小海哥后,如同靠近大海般,咸腥的味道不再长成盐晶,海的波浪也可以把他们摇去远方。
离开岛的头天晚上,我和小海哥他们坐在大广场上听外来的戏班子唱戏。台上唱着,台下的亲朋揶揄我,说城市丛林有什么好,我或许仍然是寂寂无名的“草食者”。我才发觉陆上的偏见,海这头同有。
小海哥插话替我解围,又用合理的借口拉上我跑走了。大海边我们再次玩起找贝壳的游戏,我们找到相似的贝壳,但仔细看来,自然赐予的纹路又是绝世无双。我明白他是借这游戏安慰我,不过我更惊讶于他处事的成熟远超同辈。我愈发觉得,他是父母口中有出息的人。他说以后想当医生,“做医治病还得功德”。
回到城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像头水怪堪堪变作人形难适应陆上的种种,我时常想那座小岛,那片无边海,和名字里带海字的人。
长大后为了打破当年戏台下的嘲讽,我拼命朝丛林外闯去。只是,我时常想那片海。
我回了家乡,得知小海哥高中时和家人出海,遇上风暴,用一条腿换回生命,在岛上开了一家诊所。我找过去,停在不远处看用黑色毛笔写的招牌,招牌下还有一串字介绍凉茶。我正专注看着,一个拄着拐杖的年轻人走出来。他身板挺拔,手里提着水壶,要倒水给前来的病人。我怎么看他,怎么是意气风发。
我没有上前,莫名想起那段戏词,“旧地重游,只剩得梅魂月影,依稀似梦,梦里故人无踪”。此情此景,我不知道要不要用人事全非形容,我替他惋惜,儿时志向像是被拆碎又勉强圆满,可忽然,我惊觉自己再次患上了曾经的病——怜悯的偏见。外人的评判不能替他做主,我也不能。
我最后没有和小海哥打招呼,而是再次绕去海边。经年流去,心态早已翻天覆地,我仅是平和地,淡然地,遥遥看海。
冯嘉美(24岁)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14日 0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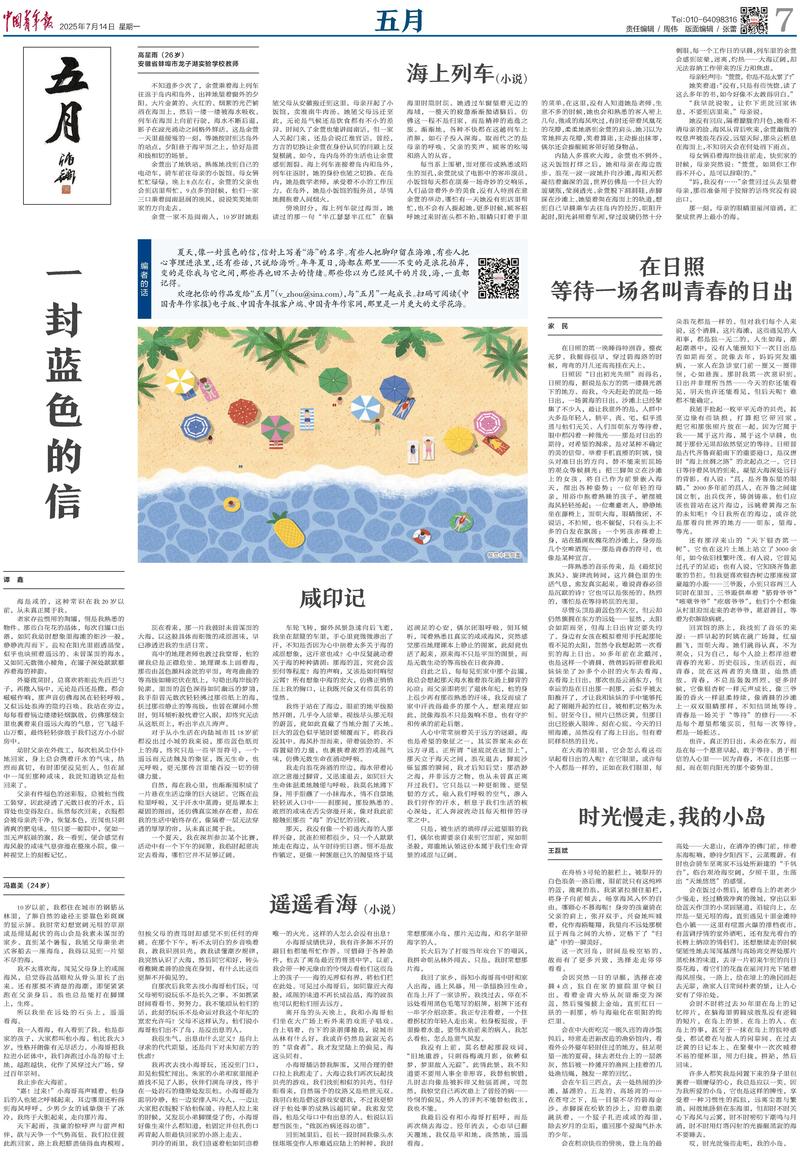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