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印记
谭鑫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14日 07版)
海是咸的,这种常识在我20岁以前,从未真正属于我。
老家存盐惯用的陶罐,倒是我熟悉的物件。那些白花花的晶体,每次自罐口出落,如同我幼时想象里海滩的细沙一般,静静流泻而下。盐粒在阳光里剔透晶莹,似乎也映照着遥远的、未曾谋面的海水,又如同无数微小棱角,在罐子深处默默蓄养着海的神韵。
外婆做菜时,总喜欢将细盐先舀进勺子,再撒入锅中,无论是舀还是撒,都会嗞嗞作响,那声音仿佛海风在轻轻呼吸,又似远处浪涛的隐约召唤。我站在旁边,每每看着锅边缕缕轻烟飘散,仿佛那烟尘里也裹着来自遥远大海的气息,它飞越千山万壑,最终轻轻弥散于我们这方小小厨房中。
幼时父亲在外做工,每次他风尘仆仆地回家,身上总会携着汗水的气味,热烈而真切,有时即便没见到人,但在屋中一闻到那种咸味,我就知道铁定是他回来了。
父亲有件褪色的迷彩服,总被他当做工装穿,因此浸透了无数日夜的汗水,后背处也变得发白。纵然每次回来,衣服都会被母亲洗干净,恢复本色,近闻也只剩清爽的肥皂味。但只要一晾院中,便如一面无声招展的旗,我一看到,便会感觉有海风般的咸味气息弥漫在整座小院,像一种视觉上的刻板记忆。
现在看来,那一片我彼时未曾谋面的大海,以这般具体而细微的咸涩滋味,早已渗透进我的生活日常。
高中的地理老师也教过我堂哥,他的课我总是正襟危坐。地理课本上画着海,那些由蓝色颜料涂就的平面,弯弯曲曲的等高线如睡蛇伏在纸上,勾勒出海岸线的轮廓。里面的蓝色深得如同幽远的梦境,我手指曾无数次轻轻拂过那些纸上的海,抚过那些静止的等高线,也曾在课间小憩时,侧耳倾听般枕着它入眠,却终究无法从这纸页上,听出半点儿涛声。
对于从小生活在内陆城市且18岁前都没出过小城的我来说,那些蓝色纸页上的海,终究只是一些平面符号,一个遥远而无法触及的象征,既无生命,也无呼吸,更无那传言里能吞没一切的磅礴力量。
自然,海在我心里,也渐渐囤积成了一片悬在生活边缘的巨大谜团。它既在盐粒里呼吸,又于汗水中蒸腾;更是课本上凝固的图画,还仿佛真实地存在着,却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存在,像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厚厚的帘,从未真正属于我。
一个夏天,我在深圳参加某个比赛,活动中有一个下午的间隙,我临时起意决定去看海,哪怕它并不足够辽阔。
车轮飞转,窗外风景急速向后飞逝,我坐在颠簸的车里,手心里竟微微渗出了汗,不知是否因为心中揣着太多关于海的咸涩想象,这汗意也咸?心中反复跳动着关于海的种种猜测:那海的蓝,究竟会蓝到何等程度?海的声响,又该是如何响彻云霄?所有想象中海的宏大,仿佛正悄悄压上我的胸口,让我既兴奋又有些莫名的惶然。
我终于站在了海边,眼前的地平线豁然开朗,几乎令人眩晕。视线尽头那无垠的蔚蓝,竟如此直截了当地分割了天地。巨大的蓝色似乎随时要倾覆而下,将我吞没其中。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强劲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也裹挟着浓烈的咸腥气味,仿佛无数生命在涌动呼吸。
我走向浪花奔涌的岸边,海水带着沁凉之意漫过脚背,又迅速退去,如同巨大生命体温柔地触碰与呼吸。我莫名地蹲下身,用手指蘸了一小抹海水,情不自禁地轻轻送入口中——刹那间,那股熟悉的、浓烈的咸味在舌尖弥漫开来,像对我此前接触到那些“海”的记忆的回收。
那天,我没有像一个初遇大海的人那样兴奋,就连拍照都很少,只一个人默默地走在海边,从午时待到日落。倒不是故作镇定,更像一种觊觎已久的渴望终于延迟满足的心安,偶尔闭眼呼吸,侧耳倾听,闻着熟悉且真实的咸咸海风,突然感觉那些地理课本上静止的图案,此刻竟也活了起来,原来海不只是平面的图景,而是无数生动的等高线在日夜奔腾。
自此之后,每每见到家中那个盐罐,我总会想起那天海水推着浪花涌上脚背的沁凉;而父亲即将到了退休年纪,他的身上很少再有那些熟悉的汗味,我反而成了家中汗流得最多的那个人,想来理应如此,就像海浪不只是轰响不息,也有守护和传承的前赴后继。
人心中常常揣着关于远方的谜题,海也是希望的象征之一,其实答案未必在远方寻觅。正所谓“谜底就在谜面上”,那天立于海天之间,浪花退去,脚底沙砾显露的瞬间,我才后知后觉:那浩渺之海,并非远方之物,也从未曾真正离开过我们,它只是以一种更细微、更坚韧的方式,融入我们呼吸的空气,渗入我们劳作的汗水,栖息于我们生活的核心深处,汇入奔波流动且每天相伴的寻常之中。
只是,被生活的琐碎浮云遮望眼的我们,偶尔也需要亲自来到它面前,宛如朝圣般,郑重地认领这份本属于我们生命背景的咸涩与辽阔。
谭鑫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14日 07版
海是咸的,这种常识在我20岁以前,从未真正属于我。
老家存盐惯用的陶罐,倒是我熟悉的物件。那些白花花的晶体,每次自罐口出落,如同我幼时想象里海滩的细沙一般,静静流泻而下。盐粒在阳光里剔透晶莹,似乎也映照着遥远的、未曾谋面的海水,又如同无数微小棱角,在罐子深处默默蓄养着海的神韵。
外婆做菜时,总喜欢将细盐先舀进勺子,再撒入锅中,无论是舀还是撒,都会嗞嗞作响,那声音仿佛海风在轻轻呼吸,又似远处浪涛的隐约召唤。我站在旁边,每每看着锅边缕缕轻烟飘散,仿佛那烟尘里也裹着来自遥远大海的气息,它飞越千山万壑,最终轻轻弥散于我们这方小小厨房中。
幼时父亲在外做工,每次他风尘仆仆地回家,身上总会携着汗水的气味,热烈而真切,有时即便没见到人,但在屋中一闻到那种咸味,我就知道铁定是他回来了。
父亲有件褪色的迷彩服,总被他当做工装穿,因此浸透了无数日夜的汗水,后背处也变得发白。纵然每次回来,衣服都会被母亲洗干净,恢复本色,近闻也只剩清爽的肥皂味。但只要一晾院中,便如一面无声招展的旗,我一看到,便会感觉有海风般的咸味气息弥漫在整座小院,像一种视觉上的刻板记忆。
现在看来,那一片我彼时未曾谋面的大海,以这般具体而细微的咸涩滋味,早已渗透进我的生活日常。
高中的地理老师也教过我堂哥,他的课我总是正襟危坐。地理课本上画着海,那些由蓝色颜料涂就的平面,弯弯曲曲的等高线如睡蛇伏在纸上,勾勒出海岸线的轮廓。里面的蓝色深得如同幽远的梦境,我手指曾无数次轻轻拂过那些纸上的海,抚过那些静止的等高线,也曾在课间小憩时,侧耳倾听般枕着它入眠,却终究无法从这纸页上,听出半点儿涛声。
对于从小生活在内陆城市且18岁前都没出过小城的我来说,那些蓝色纸页上的海,终究只是一些平面符号,一个遥远而无法触及的象征,既无生命,也无呼吸,更无那传言里能吞没一切的磅礴力量。
自然,海在我心里,也渐渐囤积成了一片悬在生活边缘的巨大谜团。它既在盐粒里呼吸,又于汗水中蒸腾;更是课本上凝固的图画,还仿佛真实地存在着,却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存在,像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厚厚的帘,从未真正属于我。
一个夏天,我在深圳参加某个比赛,活动中有一个下午的间隙,我临时起意决定去看海,哪怕它并不足够辽阔。
车轮飞转,窗外风景急速向后飞逝,我坐在颠簸的车里,手心里竟微微渗出了汗,不知是否因为心中揣着太多关于海的咸涩想象,这汗意也咸?心中反复跳动着关于海的种种猜测:那海的蓝,究竟会蓝到何等程度?海的声响,又该是如何响彻云霄?所有想象中海的宏大,仿佛正悄悄压上我的胸口,让我既兴奋又有些莫名的惶然。
我终于站在了海边,眼前的地平线豁然开朗,几乎令人眩晕。视线尽头那无垠的蔚蓝,竟如此直截了当地分割了天地。巨大的蓝色似乎随时要倾覆而下,将我吞没其中。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强劲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也裹挟着浓烈的咸腥气味,仿佛无数生命在涌动呼吸。
我走向浪花奔涌的岸边,海水带着沁凉之意漫过脚背,又迅速退去,如同巨大生命体温柔地触碰与呼吸。我莫名地蹲下身,用手指蘸了一小抹海水,情不自禁地轻轻送入口中——刹那间,那股熟悉的、浓烈的咸味在舌尖弥漫开来,像对我此前接触到那些“海”的记忆的回收。
那天,我没有像一个初遇大海的人那样兴奋,就连拍照都很少,只一个人默默地走在海边,从午时待到日落。倒不是故作镇定,更像一种觊觎已久的渴望终于延迟满足的心安,偶尔闭眼呼吸,侧耳倾听,闻着熟悉且真实的咸咸海风,突然感觉那些地理课本上静止的图案,此刻竟也活了起来,原来海不只是平面的图景,而是无数生动的等高线在日夜奔腾。
自此之后,每每见到家中那个盐罐,我总会想起那天海水推着浪花涌上脚背的沁凉;而父亲即将到了退休年纪,他的身上很少再有那些熟悉的汗味,我反而成了家中汗流得最多的那个人,想来理应如此,就像海浪不只是轰响不息,也有守护和传承的前赴后继。
人心中常常揣着关于远方的谜题,海也是希望的象征之一,其实答案未必在远方寻觅。正所谓“谜底就在谜面上”,那天立于海天之间,浪花退去,脚底沙砾显露的瞬间,我才后知后觉:那浩渺之海,并非远方之物,也从未曾真正离开过我们,它只是以一种更细微、更坚韧的方式,融入我们呼吸的空气,渗入我们劳作的汗水,栖息于我们生活的核心深处,汇入奔波流动且每天相伴的寻常之中。
只是,被生活的琐碎浮云遮望眼的我们,偶尔也需要亲自来到它面前,宛如朝圣般,郑重地认领这份本属于我们生命背景的咸涩与辽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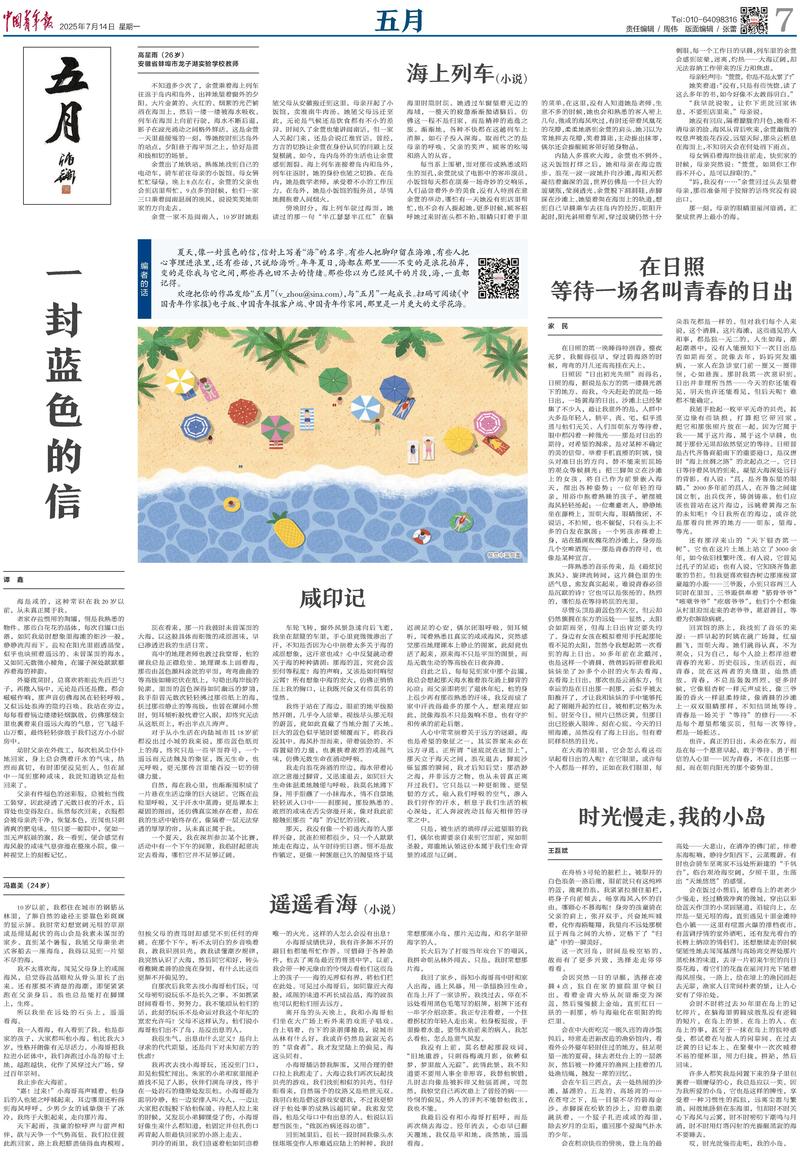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