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照的第一晚睡得特别香,整夜无梦。我醒得很早,穿过碧海路的时候,弯弯的月儿还高高挂在天上。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日照的海,据说是东方的第一缕晨光落下的地方。而我,今天赶赴的就是一场日出,一场黄海的日出。沙滩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最让我意外的是,人群中大多是年轻人,躺平、丧、宅,似乎通通与他们无关。人们面朝东方等待着,眼中都闪着一种微光——那是对日出的期待,对希望的渴求,是对某种不确定的美的信仰。举着手机直播的阿姨,镜头对准日出的方向,替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等候晨光;把三脚架立在沙滩上的女孩,将自己作为前景嵌入海天,摆出各种姿势;一位年轻的母亲,用浴巾抱着熟睡的孩子,裙摆被海风轻轻扬起;一位耄耋老人,静静地坐在藤椅上,面朝大海,眼睛微闭,不说话,不拍照,也不催促,只有头上不多的白发在飘荡;一个男孩赤裸着上身,站在插满玫瑰花的沙滩上,身旁是几个空啤酒瓶——那是青春的符号,也像是某种宣言。
一阵熟悉的音乐传来,是《最炫民族风》。旋律流转间,这片晨色里的生活气息,愈发真实起来。谁说青春必须是沉默的诗?它也可以是张扬的、热烈的,哪怕是在等待将现的光里。
尽管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但云却仍然簇拥在东方的远处——显然,太阳会如期而至,但海上日出肯定要失约了。身边有女孩在模拟着用手托起那轮看不见的太阳,忽然令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的海上日出。30多年前在北戴河,也是这样一个清晨,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看海,去看海上日出。那次也是云涌东方,但幸运的是在日出那一刹那,云似乎被太阳推开了,才让我和妹妹的手中能够托起了刚刚升起的红日,被相机定格为永恒。时至今日,照片已然泛黄,但那日出已经嵌入眼眸、刻在心底。今天的日照海滩,虽然没有了海上日出,但有着同样炽热的目光。
在大海的眼里,它会怎么看这些早起看日出的人呢?在它眼里,或许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正如在我们眼里,每朵浪花都是一样的。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清晨,这片海滩,这些遇见的人和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如海,潮起潮落中,没有人能预知下一次日出是否如期而至。就像去年,妈妈突发重病,一家人在急诊室门前一圈又一圈徘徊,心如悬旌。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日出并非理所当然——今天的你还能看见,明天也许还能看见,但后天呢?谁都不能确定。
我随手捡起一枚平平无奇的贝壳,甚至边缘有些缺损,打算把它带回家,把它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因为它属于我——属于这片海,属于这个早晨,也属于那份无果却依然坚定的等待。日照曾是古代齐鲁商船南下的重要港口,是汉唐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之一。它日日等待着风帆的到来,凝望大海深处远行的背影。有人说:“莒,是齐鲁东望的眼睛。”2000多年前的莒人,在齐鲁之间建国立制,出兵伐齐,铸剑铸鼎。他们应该也曾站在这片海边,远眺着黄海之东的未知吧?今日我所在的海边,或许就是那看向世界的地方——朝东,望海,等光。
还有那浮来山的“天下银杏第一树”。它也在这片土地上站立了3000余年,如今依旧枝繁叶茂。有人说,它曾见过孔子的足迹;也有人说,它知晓齐鲁悲歌的节拍。但我更喜欢银杏树边那座极富童趣的小殿——三爷殿,小到只容两三人同时在里面。三爷殿供奉着“筋骨爷爷”“咳嗽爷爷”“疙瘩爷爷”,他们个个都像从村里迎面走来的老爷爷,慈眉善目,等着为你解除病痛。
回宾馆的路上,我找到了音乐的来源:一群早起的阿姨在跳广场舞,红扇翻飞,面朝大海。她们跳得认真,不为观众,只为自己,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历史很远,生活很近,而青春,就在这两者的夹缝里,灿然盛放。青春,不总是轰轰烈烈。更多时候,它像银杏树一样无声成长,像三爷殿的香火一样温柔持续,像清晨的沙滩上一双双眼睛那样,不知结果地等待。青春是一场关于“等待”的修行——不是每个愿望都能实现,但每一次等待,都是一场抵达。
也许,真正的日出,未必在东方,而是在每一个愿意早起、敢于等待、勇于相信的人心里——因为青春,不在日出那一刻,而在朝向阳光的那个姿势里。
家民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14日 0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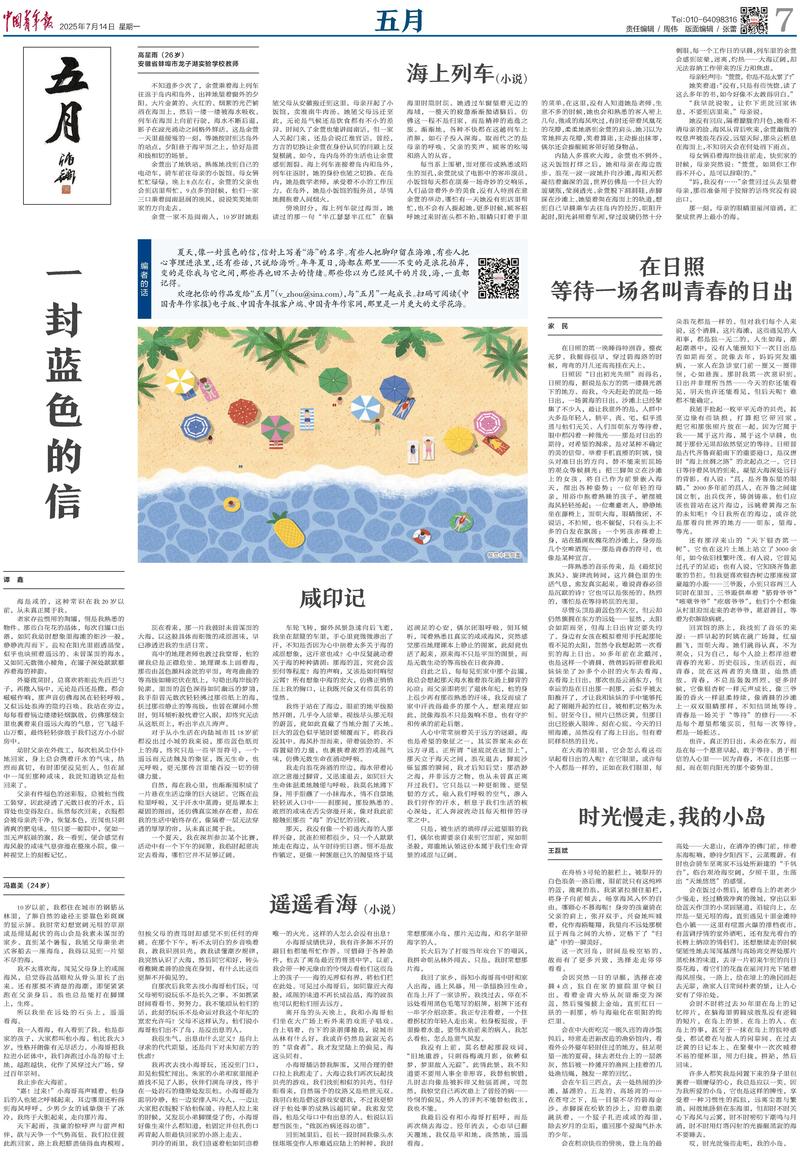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