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多少次了,余萱乘着海上列车往返于岛内和岛外,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夕阳。大片金黄的、火红的、烟紫的光芒铺洒在海面上,然后一缕一缕被海水吸收。列车在海面上向前行驶,海水不断后退,影子在波光涌动之间格外鲜活。这是余萱一天里最缓慢的一刻,等她按时到达岛外的站点,夕阳悬于海平面之上,恰好是圆和线相切的场景。
余萱出了地铁站,熟练地找到自己的电动车,骑车前往母亲的小饭馆。母女俩忙忙碌碌,晚上8点左右,余萱的父亲也会到店里帮忙。9点多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乘着闽南温润的晚风,说说笑笑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余萱一家不是闽南人,10岁时她跟随父母从安徽搬迁到这里。母亲开起了小饭馆,卖淮南牛肉汤。她随父母远迁至此,无论是气候还是饮食都有不小的差异。时间久了余萱也能讲闽南话,但一家人关起门来,还是会说江淮官话。曾经,方言的切换让余萱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反复横跳。如今,岛内岛外的生活也让余萱感到割裂。海上列车连接着岛内和岛外,列车往返时,她的身份也随之切换。在岛内,她是数学老师,承受着不小的工作压力。在岛外,她是小饭馆的服务员,尽情地拥抱着人间烟火。
傍晚时分,海上列车驶过海面,她读过的那一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在脑海里时隐时现。她透过车窗望着无边的海域,一整天的疲惫渐渐抛诸脑后。仿佛这一程不是归家,而是精神的逃逸之旅。渐渐地,各种不快都在这趟列车上消解,如石子投入深海。取而代之的是母亲的呼唤、父亲的笑声、顾客的吆喝和路人的从容。
每当系上围裙,面对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余萱就成了电影中的客串演员。小饭馆每天都在演奏一场奇妙的交响乐,人们品尝着外乡的美食,没有人特别在意余萱的举动。哪怕有一天她没有到店里帮忙,也不会有人提起她。更多时候,顾客招呼她过来时连头都不抬,眼睛只盯着手里的菜单。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老师。生意不多的时候,她也会和熟悉的客人唠上几句。微咸的海风吹过,有时还带着凤凰花的花瓣,柔柔地落到余萱的肩头。她习以为常地掸去花瓣,笑着算账,主动提出抹零,偶尔还会提醒顾客带好随身物品。
内陆人多喜欢大海,余萱也不例外。这天饭馆打烊之后,她和母亲在海边散步。浪花一波一波地扑向沙滩,海和天都凝结着幽深的蓝,世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瓶,莹润透光。余萱脱下洞洞鞋,赤脚踩在沙滩上。她望着架在海面上的轨道,想到自己早晨乘车去往岛内的经历。朝阳升起时,阳光斜照着车厢,穿过玻璃仍然十分刺眼。每一个工作日的早晨,列车里的余萱会感到眩晕,迷离,灼热——大海辽阔,却无法容纳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母亲轻声问:“萱萱,你是不是太累了?”
她笑着道:“没有,只是有些恍惚。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如今好像不太教得明白。”
“我早就说啦,让你下班就回家休息,不要到店里来。”母亲说。
她没有回应,隔着朦胧的月色,她看不清母亲的脸。海风从背后吹来,余萱幽微的叹息声被浪花吞没。远望天际,那朵云栖息在海面上,不知明天会在何处洒下雨点。
母女俩沿着海岸线往前走,快到家的时候,母亲突然说:“萱萱,如果你工作得不开心,是可以辞职的。”
“妈,我没有……”余萱回过头去望着母亲,那些准备用于狡辩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那一刻,母亲的眼睛里星河暗涌,汇聚成世界上最小的海。
高星雨(26岁)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实验学校教师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14日 0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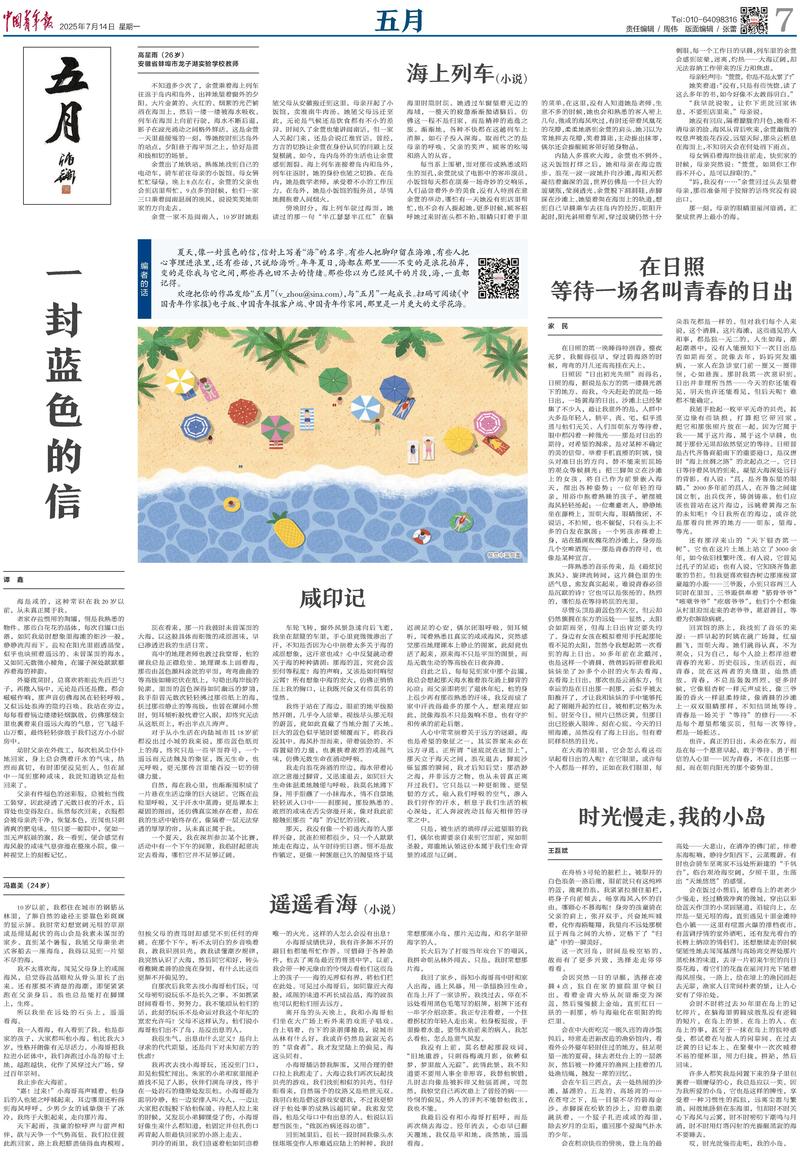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