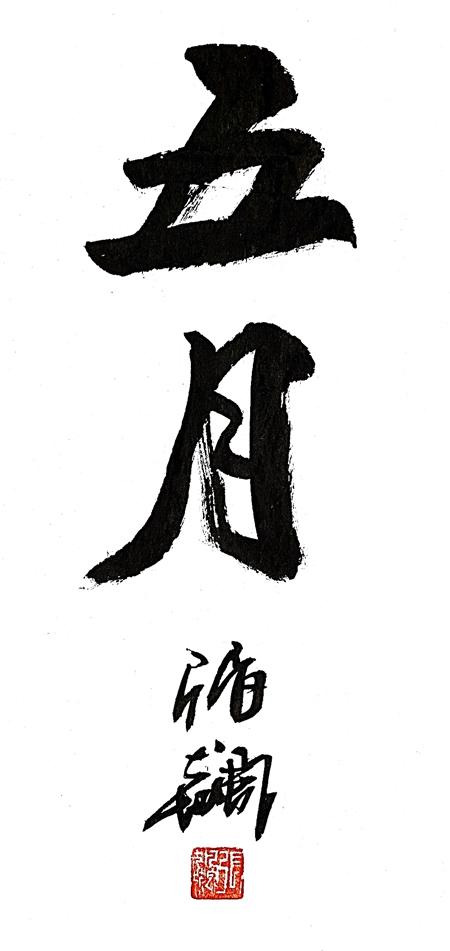

编者的话
夏天,像一封蓝色的信,信封上写着“海”的名字。有些人把脚印留在海滩,有些人把心事埋进浪里,还有些话,只说给海听。年年夏日,海都在那里——不变的是浪花拍岸,变的是你我与它之间,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情绪。那些你以为已经风干的片段,海,一直都记得。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
海上列车(小说)
高星雨(26岁)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实验学校教师
不知道多少次了,余萱乘着海上列车往返于岛内和岛外,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夕阳。大片金黄的、火红的、烟紫的光芒铺洒在海面上,然后一缕一缕被海水吸收。列车在海面上向前行驶,海水不断后退,影子在波光涌动之间格外鲜活。这是余萱一天里最缓慢的一刻,等她按时到达岛外的站点,夕阳悬于海平面之上,恰好是圆和线相切的场景。
余萱出了地铁站,熟练地找到自己的电动车,骑车前往母亲的小饭馆。母女俩忙忙碌碌,晚上8点左右,余萱的父亲也会到店里帮忙。9点多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乘着闽南温润的晚风,说说笑笑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余萱一家不是闽南人,10岁时她跟随父母从安徽搬迁到这里。母亲开起了小饭馆,卖淮南牛肉汤。她随父母远迁至此,无论是气候还是饮食都有不小的差异。时间久了余萱也能讲闽南话,但一家人关起门来,还是会说江淮官话。曾经,方言的切换让余萱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反复横跳。如今,岛内岛外的生活也让余萱感到割裂。海上列车连接着岛内和岛外,列车往返时,她的身份也随之切换。在岛内,她是数学老师,承受着不小的工作压力。在岛外,她是小饭馆的服务员,尽情地拥抱着人间烟火。
傍晚时分,海上列车驶过海面,她读过的那一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在脑海里时隐时现。她透过车窗望着无边的海域,一整天的疲惫渐渐抛诸脑后。仿佛这一程不是归家,而是精神的逃逸之旅。渐渐地,各种不快都在这趟列车上消解,如石子投入深海。取而代之的是母亲的呼唤、父亲的笑声、顾客的吆喝和路人的从容。
每当系上围裙,面对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余萱就成了电影中的客串演员。小饭馆每天都在演奏一场奇妙的交响乐,人们品尝着外乡的美食,没有人特别在意余萱的举动。哪怕有一天她没有到店里帮忙,也不会有人提起她。更多时候,顾客招呼她过来时连头都不抬,眼睛只盯着手里的菜单。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老师。生意不多的时候,她也会和熟悉的客人唠上几句。微咸的海风吹过,有时还带着凤凰花的花瓣,柔柔地落到余萱的肩头。她习以为常地掸去花瓣,笑着算账,主动提出抹零,偶尔还会提醒顾客带好随身物品。
内陆人多喜欢大海,余萱也不例外。这天饭馆打烊之后,她和母亲在海边散步。浪花一波一波地扑向沙滩,海和天都凝结着幽深的蓝,世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瓶,莹润透光。余萱脱下洞洞鞋,赤脚踩在沙滩上。她望着架在海面上的轨道,想到自己早晨乘车去往岛内的经历。朝阳升起时,阳光斜照着车厢,穿过玻璃仍然十分刺眼。每一个工作日的早晨,列车里的余萱会感到眩晕,迷离,灼热——大海辽阔,却无法容纳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母亲轻声问:“萱萱,你是不是太累了?”
她笑着道:“没有,只是有些恍惚。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如今好像不太教得明白。”
“我早就说啦,让你下班就回家休息,不要到店里来。”母亲说。
她没有回应,隔着朦胧的月色,她看不清母亲的脸。海风从背后吹来,余萱幽微的叹息声被浪花吞没。远望天际,那朵云栖息在海面上,不知明天会在何处洒下雨点。
母女俩沿着海岸线往前走,快到家的时候,母亲突然说:“萱萱,如果你工作得不开心,是可以辞职的。”
“妈,我没有……”余萱回过头去望着母亲,那些准备用于狡辩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那一刻,母亲的眼睛里星河暗涌,汇聚成世界上最小的海。
---------------
咸印记
谭鑫
海是咸的,这种常识在我20岁以前,从未真正属于我。
老家存盐惯用的陶罐,倒是我熟悉的物件。那些白花花的晶体,每次自罐口出落,如同我幼时想象里海滩的细沙一般,静静流泻而下。盐粒在阳光里剔透晶莹,似乎也映照着遥远的、未曾谋面的海水,又如同无数微小棱角,在罐子深处默默蓄养着海的神韵。
外婆做菜时,总喜欢将细盐先舀进勺子,再撒入锅中,无论是舀还是撒,都会嗞嗞作响,那声音仿佛海风在轻轻呼吸,又似远处浪涛的隐约召唤。我站在旁边,每每看着锅边缕缕轻烟飘散,仿佛那烟尘里也裹着来自遥远大海的气息,它飞越千山万壑,最终轻轻弥散于我们这方小小厨房中。
幼时父亲在外做工,每次他风尘仆仆地回家,身上总会携着汗水的气味,热烈而真切,有时即便没见到人,但在屋中一闻到那种咸味,我就知道铁定是他回来了。
父亲有件褪色的迷彩服,总被他当做工装穿,因此浸透了无数日夜的汗水,后背处也变得发白。纵然每次回来,衣服都会被母亲洗干净,恢复本色,近闻也只剩清爽的肥皂味。但只要一晾院中,便如一面无声招展的旗,我一看到,便会感觉有海风般的咸味气息弥漫在整座小院,像一种视觉上的刻板记忆。
现在看来,那一片我彼时未曾谋面的大海,以这般具体而细微的咸涩滋味,早已渗透进我的生活日常。
高中的地理老师也教过我堂哥,他的课我总是正襟危坐。地理课本上画着海,那些由蓝色颜料涂就的平面,弯弯曲曲的等高线如睡蛇伏在纸上,勾勒出海岸线的轮廓。里面的蓝色深得如同幽远的梦境,我手指曾无数次轻轻拂过那些纸上的海,抚过那些静止的等高线,也曾在课间小憩时,侧耳倾听般枕着它入眠,却终究无法从这纸页上,听出半点儿涛声。
对于从小生活在内陆城市且18岁前都没出过小城的我来说,那些蓝色纸页上的海,终究只是一些平面符号,一个遥远而无法触及的象征,既无生命,也无呼吸,更无那传言里能吞没一切的磅礴力量。
自然,海在我心里,也渐渐囤积成了一片悬在生活边缘的巨大谜团。它既在盐粒里呼吸,又于汗水中蒸腾;更是课本上凝固的图画,还仿佛真实地存在着,却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存在,像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厚厚的帘,从未真正属于我。
一个夏天,我在深圳参加某个比赛,活动中有一个下午的间隙,我临时起意决定去看海,哪怕它并不足够辽阔。
车轮飞转,窗外风景急速向后飞逝,我坐在颠簸的车里,手心里竟微微渗出了汗,不知是否因为心中揣着太多关于海的咸涩想象,这汗意也咸?心中反复跳动着关于海的种种猜测:那海的蓝,究竟会蓝到何等程度?海的声响,又该是如何响彻云霄?所有想象中海的宏大,仿佛正悄悄压上我的胸口,让我既兴奋又有些莫名的惶然。
我终于站在了海边,眼前的地平线豁然开朗,几乎令人眩晕。视线尽头那无垠的蔚蓝,竟如此直截了当地分割了天地。巨大的蓝色似乎随时要倾覆而下,将我吞没其中。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强劲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也裹挟着浓烈的咸腥气味,仿佛无数生命在涌动呼吸。
我走向浪花奔涌的岸边,海水带着沁凉之意漫过脚背,又迅速退去,如同巨大生命体温柔地触碰与呼吸。我莫名地蹲下身,用手指蘸了一小抹海水,情不自禁地轻轻送入口中——刹那间,那股熟悉的、浓烈的咸味在舌尖弥漫开来,像对我此前接触到那些“海”的记忆的回收。
那天,我没有像一个初遇大海的人那样兴奋,就连拍照都很少,只一个人默默地走在海边,从午时待到日落。倒不是故作镇定,更像一种觊觎已久的渴望终于延迟满足的心安,偶尔闭眼呼吸,侧耳倾听,闻着熟悉且真实的咸咸海风,突然感觉那些地理课本上静止的图案,此刻竟也活了起来,原来海不只是平面的图景,而是无数生动的等高线在日夜奔腾。
自此之后,每每见到家中那个盐罐,我总会想起那天海水推着浪花涌上脚背的沁凉;而父亲即将到了退休年纪,他的身上很少再有那些熟悉的汗味,我反而成了家中汗流得最多的那个人,想来理应如此,就像海浪不只是轰响不息,也有守护和传承的前赴后继。
人心中常常揣着关于远方的谜题,海也是希望的象征之一,其实答案未必在远方寻觅。正所谓“谜底就在谜面上”,那天立于海天之间,浪花退去,脚底沙砾显露的瞬间,我才后知后觉:那浩渺之海,并非远方之物,也从未曾真正离开过我们,它只是以一种更细微、更坚韧的方式,融入我们呼吸的空气,渗入我们劳作的汗水,栖息于我们生活的核心深处,汇入奔波流动且每天相伴的寻常之中。
只是,被生活的琐碎浮云遮望眼的我们,偶尔也需要亲自来到它面前,宛如朝圣般,郑重地认领这份本属于我们生命背景的咸涩与辽阔。
---------------
遥遥看海(小说)
冯嘉美(24岁)
10岁以前,我都住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了解自然的途径主要靠色彩斑斓的显示屏。我时常幻想宽阔无垠的草原或是绵延起伏的高山会是我素未谋面的家乡。直到某个暑假,我随父母乘坐老式客船去一座海岛,我得以见到一片望不尽的海。
我不太喜欢海,闻见父母身上的咸腥海风,总觉得盐晶颗粒从骨头里长了出来。还有那摸不清楚的海潮,即便紧紧跑在父亲身后,浪也总是能打在脚踝上,生疼。
所以我坐在远处的石头上,遥遥看海。
我一人看海,有人看到了我。他是彭家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小海。他比我大3岁,性格开朗像有无尽活力。小海哥把我拉进小团体中,我们奔跑过小岛的每寸土地,越跑越快,化作了风穿过大广场,穿过百年宗祠。
我止步在大海前。
“嘉!过来!”小海哥高声喊着。他身后的人也随之呼喊起来,耳边哪里还听得到海风呼呼。少男少女的诚挚烧干了冰冷,我终于大胆起来,走向那片海。
天下起雨,孩童的惊呼声与雷声相伴,欲与天争一个气势高低。我们拉住彼此跑回家,路上我把膝盖磕得血肉模糊,但挨父母的责骂时却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在那个下午,听不太明白的乡音唤着我,教我识别贝壳,教我读懂潮汐规律,我突然认识了大海,然后同它和好,转头看稚嫩柔善的脸庞在身侧,有什么比这些更解不开偏见的。
自那次后我常去找小海哥他们玩,可父母唠叨说玩乐不是长久之事,不如抓紧时间看看书、努努力。我不能顺从他们的话,此刻的玩乐不是命运对我这个年纪的宽宏允许吗?父母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小海哥他们出不了岛,是没出息的人。
我很生气,出息由什么定义?是向上寻求的代代期望,还是向下对未知前方的忧虑?
我再次去找小海哥玩,还没到门口,却见他慌忙闯出。朱家的小弟和家里闹矛盾找不见了人影,伙伴们满岛寻找,终于在一处岩石的缝隙处发现他。小海哥最为聪明冷静,他一边安排人叫大人,一边让大家把衣服脱下给他保暖。待把人拉上来的时候,又发现小弟脚踝受了伤,小海哥好像生来什么都知道,他固定并包扎伤口再背起人朝最快回家的小路上走去。
阴冷的雨里,我们追逐着他如同追着唯一的火光。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出息?
小海哥成绩优异,我有许多解不开的题目他都能帮忙作答。可惜碍于各种条件,他去了离岛最近的普通中学。以前,我会带一种无缘由的怜悯去看他们这些岛上的孩子——海的无界似有界,将他们拦在此处。可见过小海哥后,如同靠近大海般,咸腥的味道不再长成盐晶,海的波浪也可以把他们摇去远方。
离开岛的头天晚上,我和小海哥他们坐在大广场上听外来的戏班子唱戏。台上唱着,台下的亲朋揶揄我,说城市丛林有什么好,我或许仍然是寂寂无名的“草食者”。我才发觉陆上的偏见,海这头同有。
小海哥插话替我解围,又用合理的借口拉上我跑走了。大海边我们再次玩起找贝壳的游戏,我们找到相似的贝壳,但仔细看来,自然赐予的纹路又是绝世无双。我明白他是借这游戏安慰我,不过我更惊讶于他处事的成熟远超同辈。我愈发觉得,他是父母口中有出息的人。他说以后想当医生,“做医治病还得功德”。
回到城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像头水怪堪堪变作人形难适应陆上的种种,我时常想那座小岛,那片无边海,和名字里带海字的人。
长大后为了打破当年戏台下的嘲讽,我拼命朝丛林外闯去。只是,我时常想那片海。
我回了家乡,得知小海哥高中时和家人出海,遇上风暴,用一条腿换回生命,在岛上开了一家诊所。我找过去,停在不远处看用黑色毛笔写的招牌,招牌下还有一串字介绍凉茶。我正专注看着,一个拄着拐杖的年轻人走出来。他身板挺拔,手里提着水壶,要倒水给前来的病人。我怎么看他,怎么是意气风发。
我没有上前,莫名想起那段戏词,“旧地重游,只剩得梅魂月影,依稀似梦,梦里故人无踪”。此情此景,我不知道要不要用人事全非形容,我替他惋惜,儿时志向像是被拆碎又勉强圆满,可忽然,我惊觉自己再次患上了曾经的病——怜悯的偏见。外人的评判不能替他做主,我也不能。
我最后没有和小海哥打招呼,而是再次绕去海边。经年流去,心态早已翻天覆地,我仅是平和地,淡然地,遥遥看海。
---------------
在日照等待一场名叫青春的日出
家民
在日照的第一晚睡得特别香,整夜无梦。我醒得很早,穿过碧海路的时候,弯弯的月儿还高高挂在天上。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日照的海,据说是东方的第一缕晨光落下的地方。而我,今天赶赴的就是一场日出,一场黄海的日出。沙滩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最让我意外的是,人群中大多是年轻人,躺平、丧、宅,似乎通通与他们无关。人们面朝东方等待着,眼中都闪着一种微光——那是对日出的期待,对希望的渴求,是对某种不确定的美的信仰。举着手机直播的阿姨,镜头对准日出的方向,替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等候晨光;把三脚架立在沙滩上的女孩,将自己作为前景嵌入海天,摆出各种姿势;一位年轻的母亲,用浴巾抱着熟睡的孩子,裙摆被海风轻轻扬起;一位耄耋老人,静静地坐在藤椅上,面朝大海,眼睛微闭,不说话,不拍照,也不催促,只有头上不多的白发在飘荡;一个男孩赤裸着上身,站在插满玫瑰花的沙滩上,身旁是几个空啤酒瓶——那是青春的符号,也像是某种宣言。
一阵熟悉的音乐传来,是《最炫民族风》。旋律流转间,这片晨色里的生活气息,愈发真实起来。谁说青春必须是沉默的诗?它也可以是张扬的、热烈的,哪怕是在等待将现的光里。
尽管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但云却仍然簇拥在东方的远处——显然,太阳会如期而至,但海上日出肯定要失约了。身边有女孩在模拟着用手托起那轮看不见的太阳,忽然令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的海上日出。30多年前在北戴河,也是这样一个清晨,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看海,去看海上日出。那次也是云涌东方,但幸运的是在日出那一刹那,云似乎被太阳推开了,才让我和妹妹的手中能够托起了刚刚升起的红日,被相机定格为永恒。时至今日,照片已然泛黄,但那日出已经嵌入眼眸、刻在心底。今天的日照海滩,虽然没有了海上日出,但有着同样炽热的目光。
在大海的眼里,它会怎么看这些早起看日出的人呢?在它眼里,或许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正如在我们眼里,每朵浪花都是一样的。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清晨,这片海滩,这些遇见的人和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如海,潮起潮落中,没有人能预知下一次日出是否如期而至。就像去年,妈妈突发重病,一家人在急诊室门前一圈又一圈徘徊,心如悬旌。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日出并非理所当然——今天的你还能看见,明天也许还能看见,但后天呢?谁都不能确定。
我随手捡起一枚平平无奇的贝壳,甚至边缘有些缺损,打算把它带回家,把它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因为它属于我——属于这片海,属于这个早晨,也属于那份无果却依然坚定的等待。日照曾是古代齐鲁商船南下的重要港口,是汉唐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之一。它日日等待着风帆的到来,凝望大海深处远行的背影。有人说:“莒,是齐鲁东望的眼睛。”2000多年前的莒人,在齐鲁之间建国立制,出兵伐齐,铸剑铸鼎。他们应该也曾站在这片海边,远眺着黄海之东的未知吧?今日我所在的海边,或许就是那看向世界的地方——朝东,望海,等光。
还有那浮来山的“天下银杏第一树”。它也在这片土地上站立了3000余年,如今依旧枝繁叶茂。有人说,它曾见过孔子的足迹;也有人说,它知晓齐鲁悲歌的节拍。但我更喜欢银杏树边那座极富童趣的小殿——三爷殿,小到只容两三人同时在里面。三爷殿供奉着“筋骨爷爷”“咳嗽爷爷”“疙瘩爷爷”,他们个个都像从村里迎面走来的老爷爷,慈眉善目,等着为你解除病痛。
回宾馆的路上,我找到了音乐的来源:一群早起的阿姨在跳广场舞,红扇翻飞,面朝大海。她们跳得认真,不为观众,只为自己,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历史很远,生活很近,而青春,就在这两者的夹缝里,灿然盛放。青春,不总是轰轰烈烈。更多时候,它像银杏树一样无声成长,像三爷殿的香火一样温柔持续,像清晨的沙滩上一双双眼睛那样,不知结果地等待。青春是一场关于“等待”的修行——不是每个愿望都能实现,但每一次等待,都是一场抵达。
也许,真正的日出,未必在东方,而是在每一个愿意早起、敢于等待、勇于相信的人心里——因为青春,不在日出那一刻,而在朝向阳光的那个姿势里。
---------------
时光慢走,我的小岛
王磊斌
在舟桥3号轮的舷栏上,被犁开的白色浪条一路后撤,眼前就只有这纯粹的蓝,激爽的浪。我紧紧拉握住船栏,将身子向前倾去,畅享海风入怀的自由。哪颗心不慕海呢!身旁的孩童骑在父亲的肩上,张开双手,兴奋地叫喊着,化作海鸥翱翔,我望向不远处那横亘于两岛之间的大桥,定格下了“归途”中的一瞬美好。
这一次回岛,时间是极空裕的,故而有了更多兴致,选择走走停停看看。
会因突然一日的早醒,选择在凌晨4点,独自在家的庭院里守候日出。看着金青大桥从灰暗渐变为深蓝,然后慢慢披上金灿,直到红日一跃的一刹那,桥与海融化在朝阳的绚烂里。
会在中大街吃完一碗久违的青沙馄饨后,特意走进新改造的渔俗馆内,看看外公外婆年轻时住过的地方,驻足观望一池的夏荷,抹去老灶台上的一层落灰,然后被一拎摊开的渔网上挂着的几处渔结绳,触发一席的回忆。
会在午后三四点,去一处热闹的沙滩,基湖的、五龙的、高场湾的……在苍穹之下,是一目望不尽的碧海金沙。赤脚踩在松软的沙上,迎着浪潮跳跃着,一个猛子扎进咸咸的海里,除去岁月的尘垢,重回那个爱淘气扑水的少年。
会在稍凉快些的傍晚,登上岛的最高处——大悲山,在清净的佛门前,伴着东海呢喃,静待夕阳西下,云蒸霞蔚。有时也会骑车至离家不远处所新建的“千帆台”,临台观沧海空阔,夕照千里,生荡出“天地悠悠”的感慨。
会在饭过小憩后,随着岛上的老老少少慢走,经过精致净爽的微城,穿出以彩绘蓝天作顶的小菜园隧道,沿坡向上,左岸是一望无垠的海,直到遇见十里金滩特色小镇——这里有喧嚣火爆的排档夜市,有蓝调抒情的室外酒吧,还有发光看台的长椅上纳凉的情侣们。还想继续走的时候便随性地去闻闻基湖与高场湾交界处那片黑松林的味道,去寻一片初来乍到的向日葵花海,看它们的花盘在星河月光下随着海风摇曳。一路上,绘在墙上的渔民画赶去无聊,渔家人日常间朴素的景,让人心安有了停泊处。
会时不时将过去30年里在岛上的记忆碎片,在脑海里剪辑成散乱没有逻辑的短片,在岛上的景、在岛上的人、在岛上的事,甚至于一抹在岛上的独特感受,都试着在与故人的闲聊间、在过去泛黄的日记本上、在聚餐中一次次喊着不易的碰杯里,用力归拢,拼贴,然后回味。
许多人都笑我是闲置下来的身子里包裹着一颗庸碌的心,我总是应以一笑。因为我所爱的小岛,它也是这样的脾性,享受着一种习惯性的孤独,远离尘嚣与繁琐,闲散地卧躺在东海里,但却时不时关心下海风与云雾,时不时唠叨下潮鸣与月涌,时不时用灯塔闪射的光提醒黑寂的海不要睡去。
哎,时光就慢些走吧,我的小岛。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14日 0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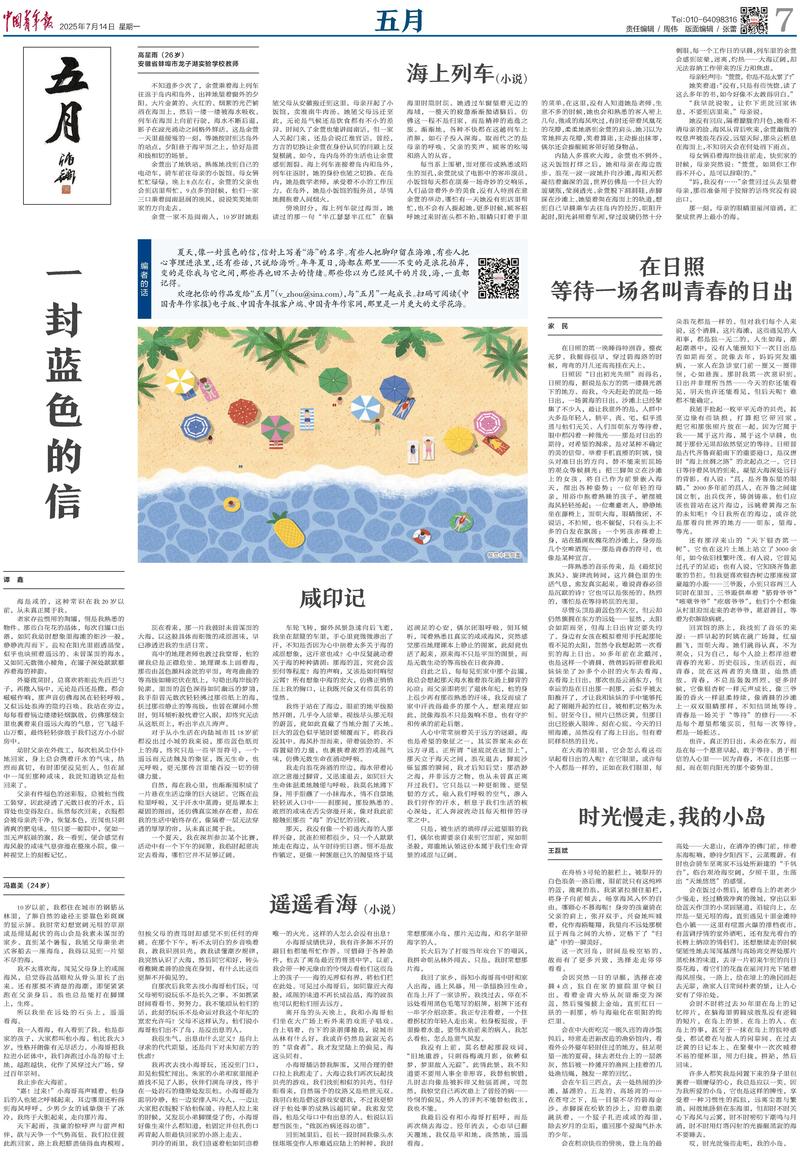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