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会想起幼年的我,经过漫长的追逐,终于抓住了一只野兔。不过在同伴簇拥过来的慌乱中,它还是从我指间溜走了。这只野兔,在我日后的回忆中,越来越像是我的童年。虽然溜走了,却在我指间留下了柔软、光滑与温暖。
童年的学校,在村子外一公里的地方,门口写着“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周边是广阔的麦田,延伸到我们无法想象的遥远的未来。当时我一直觉得,麦田的边缘大概就是星空吧。村子里的孩童们,会约着一同起床、一同上学,背着妈妈缝制的书包,像马驹一样奔跑着。下雨天,我们就望着门外,期盼家人送来雨伞和胶鞋;停电的时候,我们就从家拿蜡烛,在烛光下念诵九九乘法表。放了学,大家一起玩耍。丢手绢,这“手绢”往往是用随手摘来的嫣红色野花代替。大一点的孩子们或许已萌生了情愫,把这朵“嫣红”放在异性的身后,等待着他的发现,等待着他向自己追来。一直到夜色突然来临,我们才会结束这场游戏,把“嫣红”弃置在暮色中。因为我们明天还会再次相见,所以谁也不会觉得那朵花寂寞无主。
童年的学业,常常会被农忙打断。因为老师们同时也是农民,我们需要去帮忙。后来从县城来了一位年轻老师,他不许我们再去田地里帮忙,每天早晨带着我们跑步,跑遍了整个村子。他的家就在办公室里,窗下的书桌上堆满作业,离作业不远处是一张小床。床铺虽小,却有一张很光鲜亮丽的床单,上面绘着各种小动物,小猫和小狗并排坐着,看向远处湖泊上的月亮。老师临走时,教给我们一首叫作《萍聚》的歌,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音乐课。我们虽然不懂歌词的含义,却能感觉到悲伤在环绕,并且从窗户中绕出去,停落在广阔的麦地上。
童年是一瞬间结束的。村子里的人陆续外出打工,我父母当然也在列,他们临走时说会给我带回一个新书包。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腰上长满了疥疮。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只觉得自己肯定快要死去了;而我的父母并不在家,那个新书包是什么样子,我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了。叔叔骑着摩托车带我上街看医生,在一片暮色中我看到麦地迅速地后退,所有的一切都转瞬即逝。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我的童年结束了。
很多年过去,我离家求学,毕业后又在异地工作。但还是会觉得,我仍旧坐在叔叔的摩托车上,晚风呼啸,周边的风景和人迅速后退,一切都转瞬即逝不可捉摸。我工作的地方临靠东湖,是一片巨大的水域,比我童年时期的麦地大得多。我时常觉得,东湖是大一点的童年。我在东湖边,看着波浪的升起与降落,看着晨光的灿烂以及夕阳的浪漫,童年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影。当然我也知道,我的童年已永久地逝去了。村子里玩闹的孩童不再认识我,他们也不再玩耍丢手绢,地面上的“嫣红”随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和幻想,一起离开了。我站在曾经的那片空地上,回想我是不是也曾把那片“嫣红”放在某个女孩子的身后,她有着怎样的眼睛和衣角呢?
孙超杰(32岁)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5月26日 0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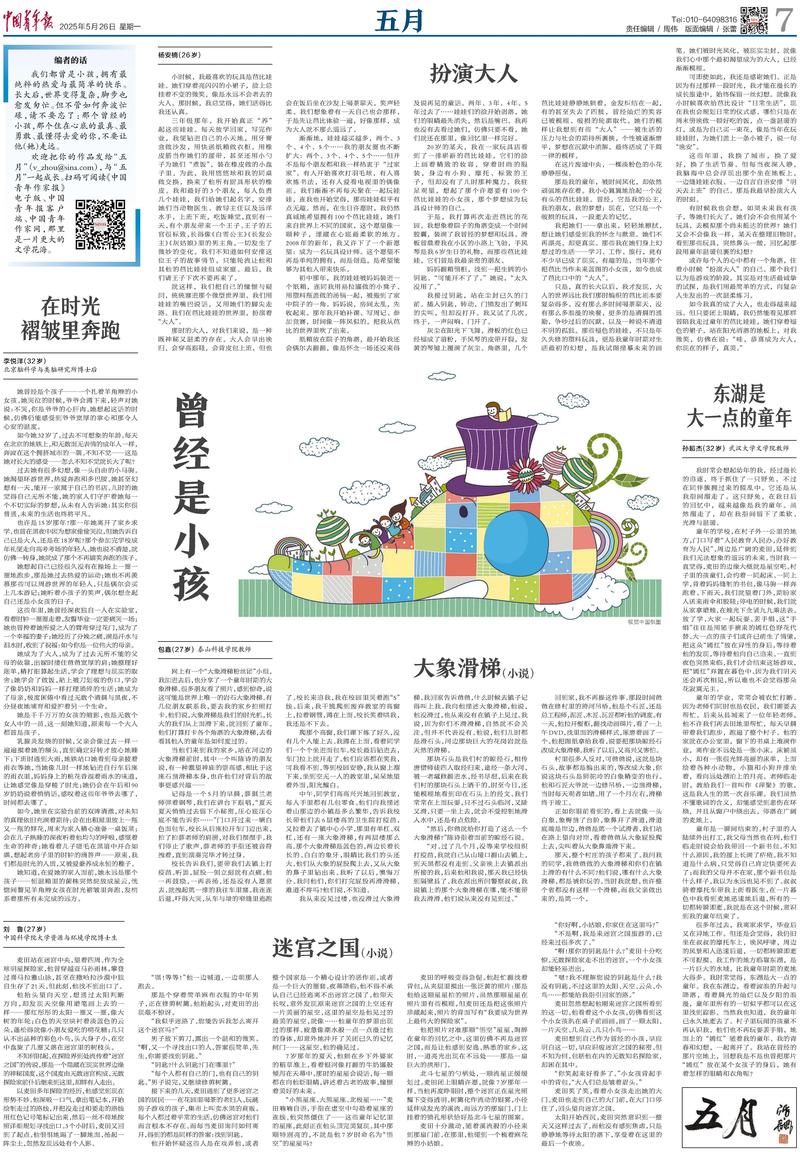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