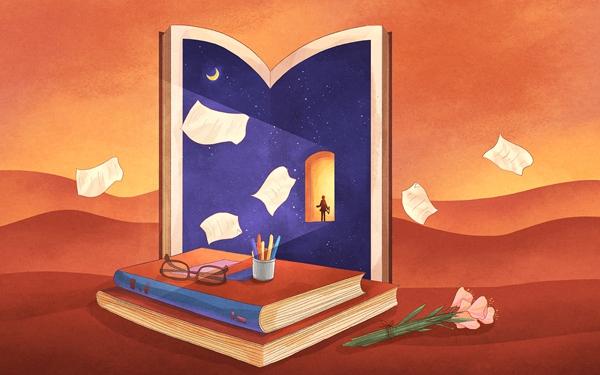
编者的话
本期的3位作家,生于不同的年代,忽培元扎根乡土,用《同舟》记录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与新生;陈崇正回望潮汕,以《归潮》钩沉百年侨乡文化的精神密码;北乔则穿梭文本之间,在《南人书话》中构建文学批评的生命对话。他们以不同的创作实践,诠释着写作者的使命与可能。在信息过载的今天,他们的实践启示我们——优秀的文学,是以独特的艺术发现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并将地方叙事转化为人类共情。这,才是文学穿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
北乔:在评论中构建文学的生命对话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伟
“我总是坚持文学评论是一种创作。如果说作家的素材是生命的体验与积累,那么文本则是作家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的结合体,评论家的评论就是以文本作为素材的创作。”
2025年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南人书话》,汇集了北乔的140余篇文学评论。带着温度和感性进入文本,以灵性的触觉探寻作品的肌理,同时又“难掩本人的性情”,这便是北乔文学评论独有的生命力。
随缘书话,触摸作品的温度
相比于此前出版的评论集,北乔更愿意将《南人书话》看作一部“散装”书评集,收录标准很朴素:没有收入其他集子里、不是太长的,且是针对一本书的评论。书中涉及小说、散文、诗歌、非虚构作品、文学史著作等评论,“虽说有些杂,但好处是视野也开阔。当然,这也让我有机会为我的读书留下了一点印记”。
对于北乔而言,写评论是纯粹的爱好,也是阅读的副产品,“书,总不会过时。那么对这些书的评论,自然也可以随书而保鲜”。他将自己的阅读依照题材分为3类,一类是出于工作需要,一类是计划之中要读的书,“这类书比较杂,但以自然、文化、社会和哲学等为主”。再有一类则是随缘而读,“大多是遇见了什么书,但凡有机会,就会翻翻,觉得投缘的,我便会细读”。
《南人书话》中收录的书评,大多便是“随缘”而生。其中涉及的作家领域广泛、年龄跨度大,不少人与北乔至今未曾谋面,但他丝毫不认为这会影响自己对作品本身的认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可以与作家密切相关,也可以独立存在,而他个人偏爱就作品说作品。“就像我去公园,可以有各种欣赏和思考,但完全可以不考虑公园是谁设计和建造的。就像我们品美食,不知大师傅,一点关系没有,当然,知道了大师傅,那也会是一种有意思。”
不过,他也提到两种例外情况,“一是作家所带有的地域文化,会让我多关注他是如何将其进行文学表达的;二是对业余作家,尤其是基层业余作家,我总怀着尊重之心和敬畏之念。他们身上拥有与众不同的温暖,因而我的评论也会带有暖意”。
与此同时,北乔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网络文学领域。传统文学之外,书中还收录了10余篇网络小说评论,其中包括“准00后”网络文学作家。北乔坦言,之所以收入这些评论,最朴素的想法是让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产生对话,“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文学形态,如果缺席,文学大生态就不可能完整”。
北乔认为,网络文学是一种“青春性的写作”,一切有关青春的心态、情绪、表达方式,与世界相处的方法等,均在其中。这些作品呈现出“年轻态”的气质和品相,是当下年轻人实时的呼吸和行走。而阅读时,他也总是试图消弭代际,尽可能回到年轻人的生活场,“感受他们的直率和勇敢,体味他们的活力和独特”。
他非常欣赏年轻创作者的活力,而他的创作,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活力。“文学是年轻的事业。这里的‘年轻’既是年龄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作家要葆有一颗童心;我们也会说,写作是一种冲动。”
好评论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多年来,北乔的创作一直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中来回穿梭,这4类文体也应合了他不同状态的思考和表达:小说,是把想说的话隐于故事里;散文,随性而语;诗歌讲究瞬时的冲击力和一定的意味深长;评论,则杂糅了以上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评论可以将感性和理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时状态式’的话语”。
北乔将评论看作自己业余创作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他的评论总能够跳出框架的限制,向着自由的方向漫步。“因为业余,我不受学术成果所限,可以不考虑学术规范,可以自由写作。因为业余,我们没有阐释理论的使命,也没有创造‘观点’的负担。”
“借着作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是北乔最喜欢的评论方式。在他看来,小说、散文和诗歌,个性化表达的色彩和痕迹比较重,评论则完全不同,“明明是我所思所想,是我要表达的,是我的观点和态度,但却假借从作品读到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挺有意思的”。
先创作小说和散文,然后才开始写文学评论,这似乎注定了北乔评论作品时总会带着“写作者”这一身份意识。不见传统评论文章的理性批评,北乔更希望自己的评论拥有对作品的一种在场性共情,“文学作品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作家生命的外溢。因而,作品是有生命的,底层的本质是感性”。
在北乔看来,评论家遭遇一部作品的历程,其实和作家相似,都是从感性抵达理性。评论家的理性思维十分关键,能够丰富和发现作品的文学品质,研究和总结作品的叙事,进而完成理论上的构建。不过,在作家为读者营建的文本世界下,评论可以高度理性,也应有作品的体温,“好的评论当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良好的互动,自然便能形成张力”。他提到,自己更喜欢“中医式”的评论,即“把作品视为生命的整体,而非各种特质性的组合”。
基于此,北乔也向年轻写作者提供了一条自己的创作路径:“写评论,先要尽可能地进入作家的创作通道,然后再抽身而出,正所谓进山看山,再在山外看山。”他进一步解释,就是要先把自己以及自己所掌握的理论丢掉,用心感受作品,如同体味生活一般。而文本细读,首先要激发自己的灵性和悟性,自己感受最深的那个部分或某个点,就是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谈及本书能为青年带来何种启发,北乔说:“对读者,我期待的是他们读到《南人书话》后,能觉得文学是美妙的,是可以读到许多东西的。书的价值,在于书本身,也在于‘我的阅读’。至于写作者,那真不好说,毕竟,写作是靠‘悟’而非‘教’。然而,《南人书话》可能的优点是我本身是写作者,那么我的评论中会有些因为他者创作而来的写作经验,或者以我的写作经验去体悟作品的叙述。但这还得靠大家去读,去悟。毕竟,这世上有太多的事只可意会无法言明。写作之事,似乎更是如此。”
---------------
忽培元:写出与时代相匹配的作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伟
“同舟啊故乡,你这百折不挠的古老村庄,宛若黄河西岸一条渡船,我为你拜地而歌……”(《同舟》)继聚焦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之后,2024年,以中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为着眼点的长篇小说《同舟》出版,这是忽培元献给家乡的心血之作,也是一部中国乡村真实的奋斗变迁史。
2019年年初,忽培元曾来到《中国青年作家报》线上“青年课堂”,与青年读者交流创作经验:“我们要立志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成为一个能够对得住这个时代,写出与时代相匹配的作品的作家,就必须要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情,充满我们自己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了忽培元工作室。采访当天,忽培元穿了一件红外套,年近古稀的他声情并茂,一口气不停歇地讲了一个多小时,那股精气神,和他书中描绘的主人公别无二致。
致敬故土,描绘农村发展现代路
《同舟》被忽培元看作是“游子献给故乡的一个敬礼”,小说中的同舟村正取材于他的家乡,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这里地处关中东府平原与渭北高原过渡地带,天气晴朗的日子,“站在院子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南面的华山与东边的黄河”,也是在这里,他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直到走出家乡,思念仍一直牵引着忽培元。如果说《乡村第一书记》反映出乡村摆脱贫穷、走上致富道路的状况,那么《同舟》便更加突出地书写了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十月的华邑乡间,正是景色迷人的季节。一眼望去,到处是现代化的设施农业的英姿。有各类蔬菜大棚,有各种果树大棚和集中连片的大面积高标准粮食作物种植示范区,还有万头现代化养牛场和粪便经过无害化制沼处理的大型现代化养猪场……”小说中描绘的种种图景,都是忽培元行走在家乡与全国各地农村时的亲眼所见。
《同舟》讲述了10年间乡村变迁的故事,而忽培元的创作也经历了大约10年的准备时间。其间,他每年都会回乡,走过熟悉的田野,看到一张张阳光下的笑脸,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也目睹了新型乡村、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到了今天,家乡已经走在了现代化农业的最前面”。
“要做一名水手,在艰难曲折中破浪前行”
从陕西省延安地区川口公社插队知青到国务院参事,基层底色一直深深烙印于忽培元的人生轨迹中。无论是《同舟》中的赵志强,还是《乡村第一书记》中的白朗,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一个好干部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一些农村中棘手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也清楚”。
不同于被中央委派到基层驻村的白朗,赵志强本是回乡做田野调查的社会学博士,却意外被推选为村主任,在艰难曲折的实践中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从“观察者”到“参与者”“建设者”的转变,扎根在与他血脉相连的同舟村。
在全国各地农村的一次次走访调研中,忽培元也见过太多像这样的年轻干部,“乡村就像一块磁石,牢牢吸引着那些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这里头有志愿者,也有回乡的青年。他们就像大树上的枝干与树叶,向着阳光生长,始终追寻展示自我的机遇,甚至要主动创造这种机会”。然而,农村的现实情况远比很多人想象中复杂,平静的表面下,往往矛盾重重,这些在《同舟》中都有体现。
“生活不是拥有标准答案的教科书,有失误、有教训,也会磕碰得头破血流,但在艰难困苦中,要成长、要充满斗志,要与旧传统和落后习俗抗争,才可能有发展。”这是忽培元的切身领悟,也是他赋予书中人物的关键课题——在同舟村的10年,赵志强带领干部群众,解决了眼前的一道又一道难题,克服了看上去不可能克服的困难,这也磨炼了他自身的意志与心性,使他从一名学者成长为有能力、有魄力的村主任、村支部书记。
“《同舟》中有很多激烈的矛盾,我们从不回避这些矛盾,而是迎着机遇和挑战向前走。赵志强这个人物,便是在直面问题和挑战的艰难前行中意识到,一名社会学家不仅是一个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生活者,是社会中的一员。”忽培元说,“我们要把自己变成真实生活中的一个水手,在风浪中勇敢搏斗,破浪前行。”
同舟村的原型,是忽培元幼时生活过的鲁坡村,而他在小说中为村子取名“同舟”,这既是书名,也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一个村子就是一条航船,村民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找到平坦的阳关大道。而掌舵的人就是我们的村干部,既要掌好舵,也要带领大家,把劲头调动起来。”忽培元说,“中国也是一艘大船,如何在世界的洪流中赶上潮头,需要齐心协力,破浪前进。”
青年作家要沉到生活的底层,锚定文学的精神坐标
在《中国青年作家报》线上“青年课堂”的分享中,忽培元曾这样说过,青年作者如果要立志成为一个合格的写作者,必须比常人更有心有意地沉到生活的底层,而作家柳青先生,就是青年非常好的榜样。60多年来,柳青的《创业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人生观,至今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忽培元看来,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精神的力量。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他对陕西老一辈作家的名字无比熟稔,“直到现在,我们也能从前人的精神中学习和获得很多东西,他们对待生活和时代的态度,对待人民的态度,对待土地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永恒要面对、要学习的问题”。
“写作的过程中,生活不断地拷问我、为难我,同时也宽厚地启发我、回答我,让我在艰难中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忽培元像是一名水手,在急流与暗礁间前行,在风雨和漩涡中校准航向,手中紧握的笔便是他的船桨。
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捧起《同舟》,忽培元缓缓开口道:“我一辈子爱文学,最开始想通过文学成名成家,后来完全是因为爱才坚持下来,现在看来,文学是一种责任,写东西要负责任。”
采访的结尾,他庄重寄语青年:“青年作者要广泛地了解生活。人都是在一个坐标系统里生活的,如果只关注自己所在的这个点,而对坐标系没有了解,写出来的东西不会具备洞察力、不会具备历史的纵深感,也不会具备更大范围的典型意义。要真正了解更大范围的生活,了解你所生活的时代、这个地球的现状,了解得越宽泛,在写作上就越有自己清晰的标准和发言权。另外,一定要真诚,我始终相信,真诚的文学是最富有魅力的。”
---------------
陈崇正:在潮人百年风雨中寻求精神合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伟
“世界教会我做事,但老家潮州一直在教会我生活。”
作为从潮州走出的作家,潮汕文化的汁液始终浸润着陈崇正的文字。长篇小说《归潮》以虚构的南方小镇潮州碧河镇为起点,围绕陈、林两家四代潮州人的百年奋斗,铺陈出一部关于“归潮”的叙事史诗。带着一份“来自故乡的重托”,陈崇正举笔勾勒出潮州的过去与现在。
“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锚定漂泊中的文化根脉
生在潮汕、长在潮汕,陈崇正的成长经历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家族的故事、长辈的言传身教,让他对潮汕人的家国情怀有了切身的感悟。“我的家族中不乏‘过番’的华侨,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
潮汕人重宗祠、守方言、敬神明,看似传统,但在陈崇正看来,这实则是漂泊者对文化身份的锚定。其中最触动他的,是潮汕人“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的执念。“无论是出海还是还乡,宗祠里的香火跨越山海,侨批中的墨迹浸透乡愁,这种对文化根脉的坚守,让我看到了一个族群在动荡中的精神韧性。”
这种血脉中流淌的“根”的意识,也通过小说中陈、林两家四代潮州人的百年奋斗与“归潮”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以“碧河书楼”和“陈家祠堂”为空间轴心,用“香炉”作为贯穿百年的象征物,串联起四代人的命运。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历史线采用全知视角,展现大时代洪流;现代线则以青年陈锦桐的探秘视角切入,通过书信、视频等媒介揭开尘封往事。
在“考古式叙事”的悬念引领下,随着历史事件的抽丝剥茧,一幅潮汕文化的基因图谱逐渐拼凑而出。《归潮》全书十几万字,却在非常有限的字数里面容纳了百年变迁中的人物群像和文化风物,如同一件木雕作品,精密而准确,这种“精巧”也是陈崇正自身最满意的一点。通过精心设计人物的命运线,他将不同时间段的故事片段像拼图一样拼接起来,每个时空的故事都有其独立的完整性,同时又在关键节点上相互呼应、相互交织,“出海和归来,过去与现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陈崇正眼中,潮汕的海洋孕育了潮汕人既冒险又保守的复杂精神,他们既敢闯南洋,又希望叶落归根。而潮汕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家族观念、拼搏精神,都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能够引发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共鸣。“就像《归潮》中林雨果这样的人物,身上正存在着人类共性。林雨果问‘什么是潮州’,实则在问‘我是谁’,这是每个当代人的命题。”
左手科幻,右手现实:书写南方蓬勃的寓言
“从半步村到美人城,我左手科幻,右手现实,努力书写南方蓬勃的寓言。”这是陈崇正对自己创作的总结。
《美人城》中的基因改造、《归潮》里的时空交织……他的小说时常游走于魔幻与现实之间,然而无论是魔幻还是科幻,都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与重构。潮汕这片土地上似乎天生带有无法解释的神秘色彩——“如果你了解潮汕文化,你就会明白这里充满了对多重宇宙的想象,走到哪里都可以遇到满天神明。”
无论是《归潮》中林阿娥穿越战火送丈夫骨灰归乡,还是《悬浮术》中在元宇宙中虚拟重建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对抗遗忘的方式——前者靠血肉之躯,后者借数字技术,但核心皆是“人如何不被异化”。陈崇正解释,从一系列科幻小说中的分身折叠悬浮,再到《归潮》中的历史回望,他其实都在用文字探索着人类的生命重心如何安放的问题。
“科幻中科技对精神的影响,与历史中文化对人性的塑造,本质上是同一命题的两面。不同的是,科幻以未来为镜,映照当下的困惑;历史则以过去为舟,承载治愈的力量。”陈崇正说。
“或许正是科幻创作恰好造就了我对‘未来感’的敏感,而《归潮》则让我学会将这种敏感反向投射到历史褶皱中,时间在故事中并非匀速前进,它可以在某些瞬间为人物的感动而停留,也可以在不经意间一掠而过。”
书写新的归潮故事:让传统文化在创造力中焕发新生
小说中,作为新一代潮汕人的陈乔锋与陈得海,都面临着传统文化继承与现代性的冲突,而在陈崇正看来,两人的命运,正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遭遇挑战的缩影。
传统与现代如何相融?陈崇正在潮州见到了答案。创作期间,他曾深入走访潮州古城,看到老宅改作茶馆,厝角头下,年轻人正在用直播推介工夫茶——“这恰是传统与现代的共生”。
“就像潮州木雕的技艺,既要保留百年刀法,又需契合当代审美;古民居修缮需保留形制,却能注入新功能。”陈崇正说,“冲突的本质是文化如何在流动中保持生命力,而非固守或割裂。真正的守正,应是让文化基因在新语境中生长;而创新,则要以传统为锚,避免迷失方向。这种困境本身,恰恰是文化生命力的体现。”
近几年,潮汕英歌舞破圈走红,风靡网络,这项绽放着野性生命力的潮汕传统艺术通过科技的传播,划破时空与地域的界限,击中了现代人对原始力量的渴望,也让陈崇正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潮汕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创造力。当人们在咖啡馆里讨论潮剧,在直播间推广工夫茶,就是在书写新的归潮故事。”
谈到家国情怀,谈到潮汕精神,并非一定是宏大叙事。在千年历史的潮州古城,这种情怀可以具象为一句方言、一碗粿条,或是一段未被AI翻译的潮剧唱词。陈崇正将观察的视角扩展到更广泛的年轻一代,“年轻人只是不喜欢繁文缛节,不喜欢各种条条框框,但骨子里对家国情怀,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要比我们想象中更高。他们可以接受英歌舞,接受哪吒,那么也必定能够在牛肉丸与潮州大锣鼓中看到时代潮流,看到炫酷的光泽”。
“是时候了,该让年轻人成为叙事主体,通过他们的视角解构宏大历史,让家国情怀从口号变为可触摸的生命体验。”陈崇正寄语有志于书写地域文化的青年创作者:“要热爱自己的土地,有意识地去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方言俚语、祭祀仪轨,甚至一碗粿汁的做法,都是打开文化密道的钥匙。要敢于打破传统框架,用年轻人的语言重构历史记忆。故乡不是静态标本,要写出它在高铁、短视频冲击下的震颤与蜕变。最后,寻找‘最大公约数’——将地方经验提炼为人类共情,最好的地域写作,恰恰是为了超越地域。真正的地域文学,既是泥土的芬芳,也是星空的回响。”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4月17日 07版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