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李福昌明显老了,他说话吞字,偶尔被口水呛到,走路一瘸一拐,脚趾肿得像紫茄子。可他的儿子说,如果社会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游戏,李福昌就是那个成功通关的“非人民币玩家”。
他一生的角色包括农民、工人、美术教师,还开了20多年面馆。几十年后达成的成就,是在西安买下3套房,为妻儿落了城镇户口,将两个孩子供上大学。
通关全程平淡无奇,类似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生。他堪称“普通”,普通到记忆被时光冲刷,最后说不出成功在何处。
幸好有日记锁定细节。过去40年每一个劳累的夜,他都在写,最终填满70个本子。载体由国营工厂的信笺变成了精装皮革本,记录者则从酒后长叹“太难活”的年轻人变成了总在笑,只顾将儿子的凉茶水倒进自己保温杯的老人。
一些东西至今仍未失效。比如将日记里每一日的不安或喜悦总结后,能看清这叶个体的扁舟,如何在非典、经济危机的浪潮中驶过。农村人在城市站稳脚跟的事,今天也仍在发生。
儿子敬佩李福昌,愈发感到自己走着类似的路,作相同的选择——这令他心安。他说自己父亲的一生,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样本,也是一个时代不应被忽视的寓言。
一
1994到2016,22年,李福昌经营着这个国家天大的事——吃饭。
日记最早的记录里,他在工厂做行政秘书,餐饮是副业。每天清晨4点擀面,然后去工厂,洗手后写厂长讲话稿,午饭前从单位提两桶烧好的热水到附近的门面。食客大多是工人,自己带餐盒,不要服务员。
上世纪90年代,工厂倒闭了,他再也不用和工友一起,苦等那些永远不会再发的工资。直到1998年,这样下岗的“李福昌”,全国上下,国有和集体企业有7000多万人。
他开了自己的面馆,在2000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说,“今天忙着招呼顾客,裤子裂了一天都没发现”;两年后的日记写道:“我非常劳累,可能哪天眼睛一闭,永远休息去了。”
他信奉着小本生意的真谛:省的就是赚的。多出来的利润包括自己充当壮劳力,亲自去菜市场买菜,一次省50元,时刻监督厨师和服务员。代价则是累,瞌睡在任意时间袭来。有次他骑摩托载着刚买的菜,倦意突然降临,一头栽在路边。菜洒了一地,行人吓傻了。他爬起来去旁边的商铺洗脸,用风油精抹到太阳穴上,收拾下走人。
另一天清早,骑车运菜时被出租车刮倒,他滚进了路边修电缆的土坑。坑有4米深,他在里面弯曲成U型,沙土进到眼里,什么都看不见。环卫工用绳子把他救了上来。还有一次失足发生在自家饭馆的临时仓库,一间没修完的毛坯房,里面有坑洞仍插着钢筋。当天生意好,李福昌冲进来拿菜,跌进去,钢筋在大腿上戳出指头粗的洞。
他至今说话仍自带手势,语调上扬,最后一字狠狠加重语气。他把这些事当作荣耀,比如自己58岁时还能拖动几百斤的货物;也是那年,为了不耽误营业,他凌晨3点起床,卸下头晚坏掉的抽风机,然后敲开维修铺,给店主递烟、赔笑、说好话,早饭时一切恢复正常。
老板操心一切。李福昌说员工“给再多的钱,也不和你一条心”。厨师偷着把面条倒进泔水桶,一天毫不节约地用掉30斤油。聪明的服务员总偷懒,木讷的则不会招呼客人,共同点是爱玩失踪——突然回老家或单飞都有可能。他曾让信赖的后生住在店里,夜里看护。后来发现那家伙偷配了钥匙,每晚从柜台里盗取10元20元,去网吧玩通宵。
日记里记录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2000年前后顾客赊账成风,他不得不在店里张贴自创的打油诗劝阻。还有瘾君子来吃面,吃完用玻璃把嘴划烂索赔;喝醉的人则在店里斗殴,把桌子统统掀翻。10年前,工商吃饭有时不给钱,市容管理的人态度恶劣。
有一次,他们把李福昌摆在室外的桌子拖走,李福昌夫妇冲上去和他们争抢,服务员都在旁边揣着手看。事后问为什么,员工说,“那是你们的桌子,又不是我的,我挨打怎么办。”
也有另一种视角。李的爱人王芝琴说,老李太凶了,说话又很大声,总在店里呵斥服务员,“你!你!快给人倒水。”这令顾客受用,却让员工焦虑。她曾看着一位刚来的姑娘绕着桌子,很搞笑地来回跑,就问她在干啥。对方很紧张,说她也不知道,就怕闲下来被骂。
“人活着就要干嘛!”他试着辩解。
李福昌在工厂时,每晚画海报到凌晨两三点,上世纪80年代做过一段时间美术教师,一天兼7个学校的课,冬天骑车来回,雪糊在脸上结块,脚也冻在棉鞋里,回家后搁在火炉边化开。
为什么这么累?很简单,真的只为钱。家里4个老人和两个孩子要供养,他不知道多少钱能提供安全感。“每天累得绝望,但是晚上把钱塞进保险柜时就很高兴。”
他从未觉得这种活法有什么不妥。唯独有一次,那是2000年的冬天,强烈的无聊突然降临,他感到必须立刻来一场娱乐,于是买了一张电影票。电影院的椅子很柔软,温度适宜,阴暗又安静,他睡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午觉,十分满足。
不过,他完全不记得自己看的那场电影是什么。也从没人问那天下午他去了哪里。
二
改革开放头些年,做生意还被人瞧不起。上个世纪90年代,李福昌在工厂兼职开饭馆,主顾大多是工人,有天工厂突然下午放假,工人回家吃饭,午餐可能白做了。于是他端着面条跑到工厂门口,逆着人流叫卖,尽可能拦住熟人。有人嘲笑他,也有人拿出了饭盒。那锅面最终卖完了。
他记得那天很希望妻子和他一起去。但王芝琴不愿意,“她觉得好丢人。”
过去20多年,夫妻间大多争吵由生意而起。比如很多顾客等着上菜,厨房端出一碗面,有点瑕疵,王芝琴会觉得“差不多”。李福昌却总喝令重做,不听任何解释,员工因此烦躁。
他们的儿子李鹤飞年少时也听过来自后厨的争吵。那是夏天,一些菜放得久,有一点味道,但算不上坏。母亲认为用水焯一下可以用,父亲却坚持要倒掉。还有父亲坚持给只点一碗面的顾客送小菜,家人和员工都觉得没必要,看不到任何利益。
20多年的日记里,只有那么一次,发生在2011年的8月19日晚上,李福昌卖了一份13元的凉菜,里面有些是中午做的——这不过分,可顾客觉得不新鲜,吃完不开心,结账时嘟囔不值。53岁的李福昌于深夜里懊恼:“根本不是因为钱……我知道错了,糊弄了客人,决不能再犯。”
“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如果有人喝醉了酒,办法是加强服务,甚至送菜,让他羞于发酒疯;有人说菜里吃出了头发、虫子,永远不要争论,永远。立刻重做一份。
生意好的年景里看不出区别。无非是其他家缩减成本,单份菜赚多些;李福昌家人气旺,薄利多销。结果差不多。但到了特定的关头,比如2003年的非典,“整条街的饭馆都空了”,他的餐厅却成了唯一不受影响的那家——大家还是要吃饭,只是怕不卫生。李福昌被信任,于是活了下来。
他说,20多年里,从没有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搬到新地方做生意,人气不旺,他在街边大声吆喝。他擅长画画,在店门前支起黑板,定期更新黑板报吸引眼球;还一度在餐馆里支一块板,顾客可以留招聘或是商品买卖的信息,也能带来人气。
西安城没禁烟时,李福昌的柜台上摆着好多打火机。看到某人想点火,李福昌立刻冲上去送一个,还能道出熟客的姓,顾客就很受用。还有一对夫妻,丈夫是残疾人,妻子推着轮椅进餐馆的院子,李福昌总跑过去帮忙。吃饭时再给男人腿上垫块布,不让他着凉。他们很感动,变成常客。
2009年相对难。金融危机越过大洋仍有余波,李福昌则因为租约到期,将店从一条只有3家餐厅的街,搬到租金更高、还要和上百家同业挤在一起的地方。李福昌那年2月在日记里写,“我要趁这段时间学习……经济形势总会好转,充实过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冬天’。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做丰富的知识储备。”这是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到形势。
其实翻过20多年的日记,李福昌几乎遭遇了普通人做生意的所有难题。只是他自己解决了,没归咎于时代,甚至没意识到这是普遍问题。他在日记里说踏实打工的人越来越难找,剪报里的“用工荒”开始登上头条。不变的是每年都给所有员工备上年货:水果糖、衣服、罐头、糕点、茶叶。他夏天买一大筐冰棍,大家围在一起吃,这样氛围很好,员工会多干几个月。城市“创卫”,厕所都要贴瓷砖。市容隔三差五抽查,增添很多成本,但也熬过来了。后来做餐饮的越来越多,用现在的话说,成了“红海”,有同行挖他的员工,让工商局来查他,李福昌心知肚明,却没感到影响。
也有人劝他转行。2003年年初,吃饭的顾客们都在谈经营,很多人注册了公司。有人让他参与集资,很快捞一笔,他在日记里写,“看似是肥肉,不知能否吃得下。”然后非典来了,泡沫也碎掉了,大多数公司眨眼间消失,人们不再讨论。身边的人还邀他去南方听课,成为百万富翁的那种——那时他不知道传销,只是下意识排斥,理由很简单:天上不会掉馅饼;就算掉了,能力不够接不住,要“家破人亡”的。
强烈影响他生意的只有房租和拆迁。临近的菜市场一个个拆掉,买菜越跑越远。城中村渐渐没了,他喜欢的那种偏僻、便宜但宽敞的店面愈发难寻。近年来所谓的旺铺,窝在高层楼下的门面房,大约100平方米,一年要45万元租金,他在日记里惊呼“真是吓人”。2009年遭遇“二房东”,租的店铺时常停电,下水道总是堵塞,喷涌秽物,顾客们在恶臭里吃饭。他实在撑不住,主动关店。
好在办法还是比困难多,直到2014年开最后一家店,他又找到满意的门面。那里偏僻,冷清,所以便宜。房东看他年纪大,心疼他,劝他三思:“之前生意都很差……”
“你看我的。我来干,生意就好了。”
李鹤飞现在也管理一家公司,他说在父亲身上,“迟钝”和“成功”不矛盾,很多事情时间久了才显露出意义。
如果去问李福昌有关时代的问题,他会开心地笑,然后给出很大的回答,说40年特别好,大家都富了。
事实上,他和时代潮流最近的一次,也完全呈现令人语塞的巧合。那是他20多年前做生意的决定。当时省里的单位要调用他,能解决他妻儿的西安城市户口,厂里却不放人。所以他在厂子开店,用工厂的燃煤和热水,不是想赚钱,求的是厂里把他赶走。
三
李福昌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上辈人对城市户口的执念。
2011年的日记里写道,“看不到任何进入城市的迹象……想起来就想哭,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回忆的时刻是1977年,那年“黑五类”李福昌高中毕业,进入生产队劳动。
读书之外,参军是离开农村的主要方式。李福昌1978年报名,和十几个年轻人在村前空地集合,部队里的军官沉默着端详。村里会计猛然将他拽出,你这是干啥?你家那成分,还能当兵?
直到1979年,李福昌报考美术学校。因为成分不好,他又一次被拒。
“你知道吗?和我爹一起画画的叔叔,早都当美院教授了。”李鹤飞说。
多年后,他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他并不怨恨某个具体的人。
进城是目力所及的唯一出路。1982年,他在书信里愧疚地告诉王芝琴,厂里暂时不招临时工,帮她找工作的事儿告吹了,两人继续分居。后来到西安的工厂,车间里“一点书都没读”的工人用恶心的话骂他,开下流的玩笑。他当上办公室主任,只是劝女工不要再偷厂里的物料,就被她男人光天化日下打。1992年工厂改制,他代表合资方办事,老领导不平衡,说他是“叛徒”,当众骂到他痛哭。
哭不仅因为委屈。他觉得和这些人不在一个世界,但因为出身低微,他要不断向上爬。
更何况,到了城市又怎样呢?还是很穷,妻儿仍旧是“农村人”。85后李鹤飞幼时去找玩伴,还能在门口听到来自大人的劝告:不要和李鹤飞玩,说话口音都不一样。李鹤飞想看看同学的玩具手枪,人家让他把手伸出来。好的,然后子弹射出,打进肉里。对方往他伤口上拍了张游戏卡片,“你走吧。”
和朋友们放学回家,其他人吃着冰棍讨论新买的玩具,他很羡慕。“不是羡慕玩具。我他妈只是羡慕他们手里的冰棍。”李鹤飞说。
后来李福昌为了督促孩子学习,画了幅画挂在家里。画上同时有高楼和土路,意思是学好就留在城里,不好就回农村。那时全国各地流行花上万元买“农转非”指标,国务院甚至于1989年发文,要求各地严控“农转非”过快增长。陕西省1988年转户7.8万人,1990年指标锐减至4.1万。
所幸这家人都留了下来。2001年,李福昌拿着一布袋10元现金买了商品房;紧接着办下全家人的西安城市户口。那天的日记是:心情好啊,从出生起就被人欺负……可算过来了。
现在是“金钱社会”了,这也是他在日记里的总结。村干部来他的餐厅,说村里在修路,希望他捐款——没问题,送上1000元,还管一顿饭。老乡知道他发了,回老家时他再借东西:要梯子,立刻给;想骑摩托,马上送来。李福昌发现,只比其他人强一点时,人们会嫉妒;如果强很多,只有纯粹的佩服。
但也没必要膨胀,李福昌更多的感受是“赚钱好难”。所以李鹤飞很久都不知道家里买了房,一家人长期住在租来的平房里。李福昌不买皮鞋,1985年买的风衣穿了10多年。不赌博,不喝酒,后来连烟都戒了。身边做生意的朋友破产、离婚,他更加小心谨慎。
为数不多带有炫耀意味的行为发生在2013年夏天,他回老家盖新房,自己睡在工地的帆布棚子里,去野地上厕所,两条腿长满荨麻疹。但他修很大的院子,给村里的民工开二三百元的高额日薪,散名牌烟。
村里人都知道了他的排场,这令他将心事放下了一些。那桩心事困扰他30多年了。妻子娘家的亲戚告诉他,结婚时,王芝琴自己推着自行车,从自家走到他村口,一直哭,委屈地哭。他从未和妻子讨论这件事。
四
李福昌人生最初的记忆是三年自然灾害。妇孺的食物包括地下的根须,榆树皮内侧刮下来的瓤。床底下塞满玉米皮,那是父亲的吃食。他用衣袖擦鼻涕,第二天醒来,沾有鼻涕的布料被老鼠啃走了。
很穷,但他感谢他的家庭。母亲是高大强硬的女人,能扛起100多斤粮食。凌晨4点起床,母亲往往满身汗地耕完一轮地,为他煮早饭。李福昌的父母都乐观,没读过书,但意外懂得鼓励孩子。他们总夸奖李福昌——哪怕只是猪草割得整齐。孩子被村邻欺负时,他们立刻站出来。这令他快乐。
日记里不乏父慈母爱的回忆。像他12岁时罹患脑炎,住院40多天,母亲一直陪在身边,用医院的茶炉煮鸡蛋,递来时总不冷不热。康复期的他莫名暴躁,功课落下被老师留堂,母亲一天天背着他出去散步,有时忧心地守在校门口。此后的人生里遇到挫折,他总以一种中国式的宿命观安慰自己:早该死掉了,父母又给了第二条命。
于是李福昌得到的优待复制在儿女身上,只是要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这也是社会风气——上世纪90年代还在工厂时,领导和他闲聊,说李福昌你很优秀,但你能买房、给家人落户,然后供孩子上大学吗?他点点头,觉得非常对。这就是“目标”了。
儿子从中考到高考的4年里,李福昌有两个版本的日记:一个是他自己的,里面充斥着普通中年男人的丧气,“为什么要活着”;另一个写给儿子,每天放在床头让他看,里面是大段大段的寄语(大部分是心灵鸡汤),穿插着每天的评价,诸如“你好棒”“爸由衷为你高兴”。李鹤飞初中时是职校的吊车尾,最后考上四川大学设计专业。亲友间轰动,很多男人开始模仿李福昌给孩子写日记。然后过了一个多月,这些人都来说:老李你真行,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李鹤飞说那些日记,其实他看的不多。高中进步是学了自己钟爱的美术,想努力了。不过他很感谢父亲,一是以他初中的烂样,大部分家庭早就放弃,没必要再投入;二是日记一直更新,他至少从父亲那学会了坚持,也知道自己被关心。
李福昌的视角更能呈现一位父亲的细腻:李鹤飞中考前压力很大,跑到空地上嚎啕大哭,李福昌其实躲在旁边的树林里偷看,但什么都不说;高中去开家长会,儿子在校门口提前等他,还备了纸和笔。这令李福昌高兴许久,觉得孩子变了,“可以放心了”。后来李鹤飞有次烦躁,说“不想在这个家待着”,他在日记里偷偷“震惊”,长久地反思,是否给的压力太大……
李鹤飞大概5岁时,李福昌带他去浴池洗澡。他不愿意,父亲哄说“沾一下水就行”。去了才发现父亲不是那个意思,于是大哭,说李福昌是骗子。这其实是一件小事,但李福昌感到“警醒”,原来孩子如此将父母当真——于是他戒烟戒酒,不再打牌;开始夜跑也是为了做榜样;后来李鹤飞上高中,他晚上连电视都不看了。
两个孩子都变得懂事,考上大学、研究生,找到很棒的工作,李福昌生活的重心又倾向赡养老人,“尽孝要趁早”。强烈的感受最早来源于老丈人的离世,他在日记里写:
“看到芝琴的脸庞,我身上的肉都在抽动。回忆起坐在灵堂那伤心的表情,我的心都碎了……我要全身心地将任何苦难挡在身外,不能让她受苦。”
丈人、丈母娘、父亲一个个离去,只剩下自己的母亲,一代人要彻底告别了。那无疑是他生命里极度重要的事。2016年的日记里充满了细节,他记录最后一天,“像夏日的黄昏缓缓降临了,母亲到临终时,一心不乱,天心月圆……来不及对娘十分的表达,来不及实现诺言,来不及给娘最后的拥抱,很多话来不及听……”
李福昌2016年彻底关了餐厅,不再经商,和母亲、爱人一起回了老家那栋修好的大宅,给母亲洗脚,看着她微笑着入睡,在大树的荫蔽下乘凉,听她讲自己的一生,陪她拜菩萨、给舅舅送纸钱,做许多说不出意义的事。
那几个月,他画了200多张速写,主题全是母亲。老人努力从床上坐起,端着饭碗微笑,执着地戴着花镜做针线,蜷身在角落里拾掇“百宝箱”,享受儿媳的按摩。画的空白处有李福昌的随笔,大多平静安详。
但他又在日记里摘抄,说死亡肉眼可见,缓慢但不可抗拒,如同阴云压顶。他记录母亲激烈呕吐,被疼痛折磨得大喊,向医生尽可能夸大自己的痛苦。这时的李福昌会羞愧,感到“母亲还没有活够”。所有记录里有阴暗,也有快乐。痛苦是长久的底色,快乐是偶发的高潮。但苦太多,快乐反而值得浓墨重彩。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母亲告诉他:“我把你养成了,我没有遗憾。”到了晚上,受疼痛困扰,长期坐着休息的母亲说,今晚想被平放,她要舒服地睡。
五
日记里偶尔也有不一样的细节。2016年中旬的某日,李福昌写道,“晚上第三次给老娘洗脚,她心里明白,就是不心疼我……”
后来,“不”字被重重涂掉,接下来的抱怨话也被修改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几例:和妻子吃饭,发出声音被嫌弃,“她还要学一学,我非常(不)讨厌。”那个“不”字加得过于刻意,并不难识别。采访最后一天,记者提出这些。李福昌愣住几秒,回答说她们毫无疑问是他最爱的人,愤怒、忧伤也是真的。只是两三天之后再看那篇日记,会觉得当时的情绪很突兀——她们还是那么可爱,所以就改掉了。
日记里也记载了很多伤害他的人,比如当面交好、背后辱骂他的工友,不顾情谊突然失踪的店员。可那位前雇员又在李福昌开新店时帮了大忙,曾经交恶的人也恢复往来。他在上世纪的日记里抱怨,工厂里的老同志很不好,处处针对他。2012年翻看时忍不住加了批注,“难以想象。我当时确实没有尊重到位,让老同志很没面子!!!”
他说人性是善的——看陌生的食客们就行。他们从不吝惜夸赞美食;李福昌总害怕故意遗失财物的“碰瓷儿”,但没有,失主都千恩万谢;后来他在餐厅办黑板报,重拾绘画,真有人在店门前不留名地放块黑板……但他又说除了直系亲属外,所有人都是“利益关系”。
近些年他为环卫工和学校的孩子画像,有对社会的感谢,但更多是“自己老了,想留下些东西”。这两年自费跑去青岛,帮残疾人夫妇开面馆,凌晨四五点起床操持一切,除了善心,也归咎于放不下经营的本事,还想过开店的瘾。他习惯了对一切乐观,但本质上更相信自己。
他也从未感到生活到了“完美”的境地。母亲去世后,兄妹几人鲜少联系。没处理好亲情,李福昌感到遗憾。他在日记里频繁许下开酒楼的宏愿,到2016年不了了之。
如今的环境已令他陌生:租金成本飞涨,网络和连锁也摸不透……所以“东山再起”只能搁置,虽然他“还有很多做生意的好点子没有实践”。
何况王芝琴坚决反对他继续经营。她骂他是骗子,曾经约定的周游全国毫无实践的苗头。骂到老李也开始反思:他做老板有成就感,有乐趣;妻子似乎只感到压力,一直在干活。可能是该妥协了。日记里的经历愈发少,感悟愈发多。他有一天写: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后悔”——凡事都该考虑清楚再做了。
李福昌自嘲在家里也没地位。儿女长大后回家聚餐,妻子只招呼他们,为他们夹菜,李福昌仿佛不存在——他一度为此生气,后来想开了,觉得这就是家。所以现在聚餐,到了饭点,李福昌在书房写字画画,出来才发现其他人早已动筷。他就在旁边“嘿嘿”地笑,赶紧拖出凳子坐下。
李福昌确实慢下来了,他说“心轻者上天堂”,给年轻人讲俗套的寓言:上帝许诺一个人,跑过的地方都属于你,于是那人就累死了。2015年,他重拾画笔,在店门前堆积的啤酒箱子上搭起画架,慢慢回忆结构和线条。这又成了他如今最主要的消遣,作画时的投入与兴奋与40年前没有区别。
“该停就停下来。”和所有人一样,他的身体紧随年龄报警。牙疼、感染、头晕耳鸣、容易感冒,体重需要控制,腿脚越发疼痛。他每天清晨做200下高抬腿,120次踮脚,50个深蹲;再配上5~10公里的夜跑。他坚信运动能促进代谢,长出新的细胞;每晚反复着痛到极点然后麻木,战胜疼痛的过程让他心安。这是他对待不完美的方式,是他一生的习惯。
晚上,他把肿胀的双脚放进热水,用木铲上的粗糙锯齿戳那些敏感的穴位。他再次感到疼痛,然后涌出舒适。妻子去儿子家照顾刚出生的孙子,客厅里只有他自己。他曾为这双脚担忧,时至今日却丝毫不害怕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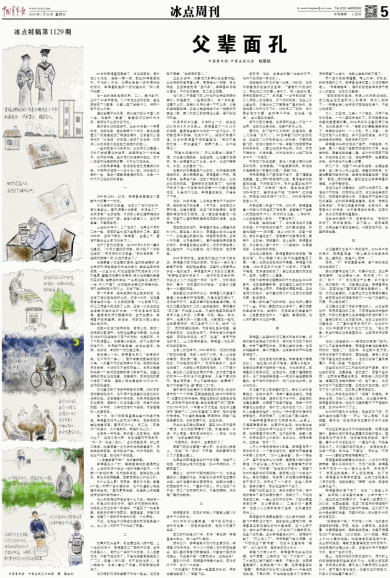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